年关将近,农村的日子也繁琐而有规律地重复着。母亲下午从镇子里赶集回来,怀里揣了一瓶墨汁、一支毛笔,还有五张大红纸。我心里暗自窃喜,已经六旬的老母亲终于又要动笔写春联了。可不觉又心起忧郁,上一次见到此番情景还在儿时。或许,那时母亲的头发还未花白吧!
乡味难愁
母亲生养我时已经是42岁,正值炎炎酷暑,农活儿要紧时分。那会儿,父亲还在村子里的国营煤矿做营生,算是有份不错的收入,所以在姐姐3岁时家里便“暖了窑”(方言,即乔迁)。很庆幸,我也成了兄妹中唯一没住过爷爷留下的老岔窑的娃。
虽说没住过岔窑,可接生的人却未变,还是我的姑姑天汝。听母亲说,生我时已是后半夜,因为我闹腾,肚子已经疼了好几天,姑姑费了老半天才接生下来,母亲也因此落下了病根子。天汝姑姑每次碰面,总要叮嘱让我好好孝顺母亲,因为我算是她接生过的最难养的娃。
农村妇女没有多娇气,尤其是我的母亲。这位生性要强的农村妇女头天晚上生完娃,第二天一早便又带着几个哥哥下了地,只用红绳一把将我拴在炕上,留下4岁的姐姐来照看我,给我洗尿布。因为上头还有3个哥哥,生计艰难,于是父亲晚上从矿上回来,就和院子里的邻里们商量着要把我送人。托本地的亲戚问了几个月,似乎,也有一些人家正在寻找养子。只是后来,母亲终于还是不忍心了:“这小子命里要在咱家,你就断了送人的念头吧!”
同年,父亲戒了烟,母亲却开始抽起了烟,直至现在。爷爷从地里挖了一株椿树种在家门口,劝爸妈说:“茶系米(方言,孩子们)不要怕受罪,好好活,活法总会好起来的。”日子就这样又开始了,一家七口成了聚财塔最大的住户。可谁曾想到,就是这样的家境,父母亲硬是用一股子韧劲儿活出了个样子——将近五旬的父亲没有被肩上的担子压垮,母亲也把我们几个儿女该裹(方言,抚养)得妥妥帖帖,每年秋收后家中瓷瓮里打下的粮食也常常有余。
那根绑过我的红绳,现在还静静地躺在炕头,它见证了我们兄妹5人的儿时;现在,又拴在了外甥女点点的身上。点点每次来婆婆家(方言:姥姥家)还总要戏耍一番。一晃多年过去,母亲当了奶奶和婆婆,我也当了叔叔和舅舅。
故土浓情
黄土地上的乡村,远没有江南水乡那般富有诗意,却也不失它独有的旷达。一孔砖窑能锁住一个人一辈子,却没有人去打算记住它的平生。可就是这样的故事,在每一道山岭上的家家户户间不断上演着。在我们看不见的角角落落,那些渐渐被黄土覆盖住的人,他们每天不停地重复着同样的动作,每次见面时寒暄着同样的话语,不觉若有所失。因为,他们对于活着的认知,已经同这片土地达成了某种契约。他们一辈子都在向这片土地索取着、倾诉着,也早已与黄土地融为一体,从来都不会畏惧死亡。
若有客人来访,母亲最爱拿出来招待的,当属扁食。这种如今再普通不过的面食,在母亲眼里,仍算得上庄户人家招待亲人和远方客人最好的饭食。犹记孩童时,经济拮据,一锅汤面里只零零散散漂着几个扁食,掌勺的母亲尽可能地给我们兄妹均匀分配。每逢过节,总有三两乞食者上门乞讨,对此,母亲也从不吝啬,每次都会给他们的瓷碗里盛满饭。这种善举延续至今,也在日后成长的道路上深深影响着我们。
对于乡村的定义,其中的味道总会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发生变化。小时候,被层层山峁包围的小村庄就是我认知的全部。农田里的秸秆和土坡上砌成的“小窑洞”总能带给我们源源不断的欢乐和喜悦。还有那些一起“过家家”的童年玩伴,随着时间推移也早已经渐渐分离,逐渐断了联系。那时,院子里养的老母鸡,已经记不起曾经几次因为觅食,被我们困在事先支好的竹筐下。还有一起光着身子戏耍过的后窊浅滩,现在也早已被煤矸石覆盖。所以,对于故土的印记总是复杂的,它不可能停留在某一个节点上,却往往又因一两个节点而萌生出更加深刻的情绪来。当皱纹偷偷爬满父母的额头,当爷爷奶奶被棺椁装殓永久地沉睡在黄土地,当黑夜吞噬掉一个个渐渐消沉的黄昏,故乡的一切都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尽管很难适应,却又无从选择,怕是感慨,怕是无奈,怕是惋惜。
再难逃离
求学生涯使我远离了这片土地,又使我对它的感情更加真切。不管对未知的远方多么渴望,离开时总会带有一丝感伤,尤其是回头瞭望到石头畔父母亲送别时的目光。而每次归乡,喧嚣的班车里那些久违的乡语情结中,谁又会看到那凸显出来的自己是多么孤独。是的,与故乡的隔阂就是在这趟乡村间跑了多年的班车中产生的。它破旧的躯壳来回穿梭在越来越平坦的公路上,里面坐着的人却日渐苍老。当老者们卷烟散出的味道弥散在车厢内,似乎没有谁会刻意捂住鼻子,因为没有谁会刻意远离那种故乡的烟火味。
缘于儿时对故乡根深蒂固的记忆,还有老祖宗留下的规矩,不管时代如何发展,总能从点滴小事中读出父辈们坚守的那份纯朴与厚重。而年轻的一代又总是有意无意地想去跟这种“权威”挑战,或许,打破也是迟早的事吧,随着他们的老去,那些琐碎的老规矩也终将会被后辈遗忘。几月前,母亲来电说,家族里的刘氏祠堂已经修就,族谱也已编修完善,村里人为此还刻意庆贺了一番。其实,已定居临汾的琴琴姐(按辈分本应叫姑姑)先前早已告知了我。不由得心想,倘若活出个样子来也罢,不然,那些漂泊在外的游子,那些被土坯墙垒住的农人,一辈子都在为生计而奔波,又哪有闲工夫坐在祠堂里给后辈儿孙讲碑文里那些逝者的故事呢?可人生一世,总得给自己找一个归宿吧!这份安稳不分贵贱,不论早晚,总归会在生命的某个角落驻足等待。
难别故土,难舍乡愁,漫步空旷的山野上,翻过一道道山峁,与黄土再遇,即便再荒芜,再凄楚,心间也足以富饶,而对未来的呼喊,只有北风能听到,只有劲草能知晓。
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15级学生 刘亚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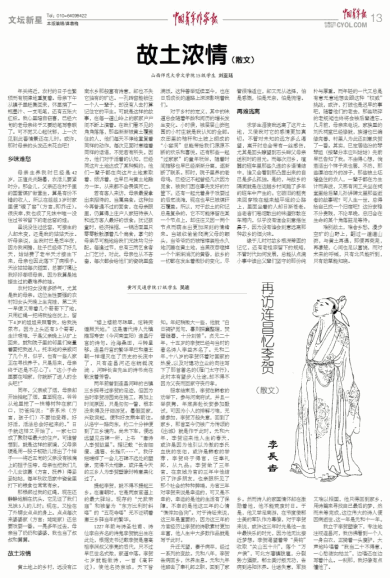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