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近日闲坐,想起了一桩旧事。
我读中学那会儿,只有周末才能回家吃饭。有一天吃饭的时候,母亲无厘头地来了一句:“听你五姨说,梁芸跟她妈吵了一架。”我盯着盘子里的肉,出了半个耳朵听了这句,本能地答道:“哦,正常,叛逆期嘛,母女哪有隔夜仇?你怕我也跟你吵架?”我拿出招牌笑容咯咯几声,把看上的那块肉塞进了嘴里。
母亲顿了一下:“是没有隔夜的仇,可这还没隔夜呢,她妈就没了……”她象征性地扒了口米饭。我放慢了咀嚼的速度,嘴里这块肉像蜡块一样,嗓子里的话被堵得说不出来。憋了半天,我认真地咽了一口饭,好不容易挤出来一个“哦”。
我记得梁芸,她是我五姨邻居家的女儿。我小时候常去五姨家,见过她许多次。那个女孩儿,走路的时候下巴微微抬起,像跳芭蕾。辫子高高地扎在头上,编成麻花状在腰间来回摆动。她身材细长高挑,长着一张学霸脸。她的身世,是村里公开的秘密。父母不能生养,从外地抱养了她,只这一个女儿,不要命似的疼着。
“听你五姨说,她最近考试不太理想,她妈说了她两句。也不知道她是从哪儿听来的,脾气上来冲着她妈就大叫:‘我又不是你生的!不要你管我!’哐当一声就把门关上了。她妈很伤心,觉得有点头晕,过了一会儿头又很疼。听说前段时间也疼过,一阵一阵的,以为是累到了,休息休息就好。结果那天晚上,就一直疼,越来越严重。夜里三点她爸送她妈去了医院,到那儿就抢救,没到5点人就没了。也不知道是脑梗还是什么的,总之人就是没了。”
母亲一边吃饭一边补充着故事的细节,像往装满黄豆的罐子里塞沙子。“你说,她是不是很遗憾,很后悔?”母亲找不到更多合适的负面词句去形容这件事情,不断地反问我。我木讷地点头,一口菜没吃把剩的半碗饭慢慢吞了下去。
二
听到这个消息后,我准备去看看她。
我敲门,清楚地听到她穿着拖鞋匆忙来开门的声音,我准备好笑容,想让一切看起来十分自然。
铁门吱呀一声拉开,她的月牙眼笑成了缝儿。“余依姐!你怎么来啦?”
我一愣:“刚到外婆家,来找你玩儿。你最近怎么样?”
“好得很呢,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准备出去旅游呢,你说是去苏州好还是杭州好?我知道你常出去,给我点建议呗?”
“你哪有时间出去啊,你都要中考了。”
“中什么考啊,姐你好糊涂,我高考都结束了。我妈挺想让我去苏大的,但是我分儿不够。不然,我去苏州怎么样?就算没考上,我也能去看看……”她挽着我朝屋里走去,还顺手帮我扯扯裙角。她的房间点缀着淡淡的橘粉色,床上放着几本《中国国家地理》杂志,刚好翻到苏州园林这一页。
“哦,既然是阿姨曾经的愿望,那你就……去看看?”我翻着杂志,装作不经意地开口。言语的侧面,我又以试探的口吻提起她妈妈,生怕突然触到她的敏感神经,扯出一串儿眼泪来。
“她现在也这样想!”我还没回过神儿,梁芸便朝着门口抬头笑起来。“妈!你今天下班这么早啊?”
我回头,梁芸妈妈站在门口,是旧时的温柔模样。“妈!我跟余依姐正商量呢,我准备去苏州看看苏大,过几年我考研究生还是可以的嘛!”
“妈只是给你建议,又不是非要你去。这丫头傻的!余依啊,中午在这吃,我刚买了鱼。”我应着,来回瞧这母女俩,骨子里的热情真像亲生一般。
三
忽然惊醒,我不断回想刚刚那个梦。
客厅里传来了几声闷闷的敲门声,犹犹豫豫地时不时来两声。
“谁啊!”我从被窝里探出脑袋,妄图用这一声应答拖住门外的人,好在被窝里再挣扎几秒钟。
没人应答,又传来闷闷的敲门声。我猜可能是快递员或者是送外卖的人敲错了门。于是我就拿出消费者理所当然的“气魄”和“鼻孔看人”的气势,套上外套去开门。结果我朝猫眼一望,听到隐隐的抽泣声。
“余依姐,我是梁芸。”
我轻轻拍着她的肩膀,心里有些数,嘴里还是问着“怎么了?怎么了?”我这一问不要紧,她的眼眶本就是负隅顽抗的堤坝,顷刻间被眼泪击垮。梁芸的嘴巴很干,嘴唇和鼻子上起了一层干燥的皮,看样子是迎着风一路哭过来的。
“我,我妈去世了……”她一字一抽地说着。我拉她坐下,倒了一杯热水放在桌子上,温水洗了一把毛巾给她擦眼泪,又把郁美净放在她手里。
“我知道,我知道,不哭了啊。”我手忙脚乱地用毛巾去接她的眼泪,不留意洪水便能淹到五楼。
“我爸说,是我把我妈气死的……我……我没考好,还跟她吵架。过了年就中考了,我爸说你成绩好,让我来问你借书。”她抽抽搭搭地说,喝了一口水接着哭。
“哦哦,好好好,我要初中的书也没用了,我以前的复习资料都给你。你别……别哭。”我渐渐感受到最后两个字的无力,吐出来的时候格外轻。我叹一声,双手撑了一把腿站起来,到柜子里去给她找书。我翻着曾经的课本,回想起自己读初中那几年的快乐,鼻子一酸竟落下两滴泪来,刚好打在了那个“余”上面。
我回客厅的时候,梁芸喝完了杯子里的水,也不哭了。我竟觉得她变成了大人,眼神充满穿透力。我把书放在茶几上,蘸了一些郁美净点在她的脸上和手背上。她伸手抹开,看了我一眼,欲言又止。
吞了一口口水,梁芸开口了:“姐,你说我要是不跟我妈吵架的话,她是不是不会这么快就……”我又想起母亲说的那句“很后悔”,可是这样一错永错的事情,哪里有什么“如果”可言?
那天梁芸告诉我,其实她早几年就知道自己不是父母亲生的,但父母对她一直很好,她并没有过于在意。
四
我再次去梁芸家的时候,碰巧她在镜子前梳头。
她原本高高长长的麻花辫,如今剪成了刚刚够扎马尾的短发。她的房间多了一张床,比原本显得拥挤了许多。看她床上的被子和床单缠在一起,旁边还歪歪倒倒地放着几个玩具汽车,一把小水枪。
我笑问:“最近怎么晒黑了?”向来爱惜自己的梁芸,可从来没任由自己在太阳底下暴晒过,出门涂了防晒还要撑一把遮阳伞。
“我弟弟,他非要去游乐场玩。我大姐二姐,一个要带孩子,一个要上班。我放了暑假,爸妈就让我带弟弟。这不,大热天的接连玩了好几天。我在太阳底下蒸着,没两天就黑了。”她梳好头,洗了一把脸。一个黝黑的小男孩跑过来叫姐姐,满头是汗,梁芸顺手也给他擦了一把。
“姐姐姐姐,收辫子的来了!”小男孩蹦着跳着,指着梁芸的后脑勺,又在自己的头上挠挠。
“姐的辫子前天才卖掉,你让我现在还能拿什么去卖呢?”梁芸对我说,她妈劝了她不少回,让她把辫子卖掉,最终卖了130块钱。后来妈妈说帮她收着这笔钱,只给了她10块钱。
“梁芸,我给你带了《中国国家地理》,就是这个月才出来的。”我见她洗过脸空下来,见缝插针说了一句。
“余依姐,谢谢你啊,你还是带回去吧。你上回给我的那本,被我弟弟撕坏了。我吵了他两句,我妈说我以后少拿那些东西回来。对不起了……我知道你想着我。你看我天天带着他也没时间看。”她的口吻,像极了上个世纪的童养媳。哪怕被责骂几句,也要爬起来蹑手蹑脚地赔笑脸。
“过两年高考了,我妈想让我考滁州学院。离家近,毕业了可以回家工作。等我弟大了,我们姊妹几个可以一起给他买房。”她弟弟听到买房,立刻嚷嚷买房!买房!
“其实我真羡慕你。你家就你一个……”弟弟缠着她,拉她去玩院子里的水龙头。梁芸回头看了我一眼,脸上写着抱歉。我以微笑回应她,朝院子外面走去。
忽然,院子消失了。我望着天花板,知道自己又梦见了她。
尾声
我终于从被窝里爬出来,握着玻璃杯闲坐在阳台。大雪铺满我的窗子,纷纷扬扬像人间的离别。
我又想起3年前的这个时候,梁芸哭得梨花带雨来敲我家的门。隔着落雪的声音,我似乎又听见了沉闷而又犹豫的敲门声。
吃晚饭的时候,母亲对我说,梁芸去年高考考了二本,不知道志愿填到了哪里。如今她独自在外念书,她的父亲又找了一个女人。
南京晓庄学院本科生 高星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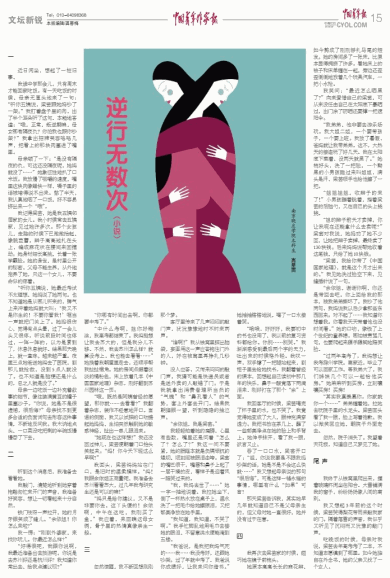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