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文学辞典里,诗歌属于青年,小说属于中年,而散文属于老年。单就“诗歌属于青年”这一条来讲,在青年时代,李白写出了《上李邕》那样传世的名诗,徐迟出版了诗集《二十岁人》,海子向世人奉献了很多精美的短诗和几部史诗性长诗,举不胜举。新时代中国青年诗人,尤其是“90后”诗人,更应该写出既属于自己、也属于这个时代的代表性诗篇。
对新时代中国青年诗人来讲,已经不是“诗人何为”的问题,而是“诗人如何大有作为”的问题。这句话的潜台词是,新时代中国青年诗人还没有写出令人引以为傲的代表性作品。换言之,新时代中国青年诗人还没有写出与新时代相匹配的精品力作。
那么,新时代中国青年诗人如何才能写出优秀诗篇、乃至不朽诗篇呢?这是新时代摆在中国青年诗人面前的重大课题,值得大家深思。总体来说,新时代中国青年诗人,学养较好、起点较高,把诗写得太像诗,在诗艺和诗思方面都很“顺溜”。有人斥之为“浮先锋”,有人责之为“研究派”。他们到底有没有形成文学史意义上的诗歌流派,这是另一个话题,暂不深究。所谓“研究派”,我想不外乎两层意思,一是依据某些主流刊物的发稿趣味,他们“有的放矢”地写作;一是按照他们所理解的中外现代诗歌传统技法,他们“像模像样”地写作。无论说他们是“浮先锋”也好,还是称他们为“研究派”也好,他们的这类写作不接地气,罕见灵气,更匮乏生活底子和生命体温。
面对此情此景,虽然我们也觉得应该给青年诗人以一定的时间,但是我们无不忧心忡忡,并试图破解这一新诗发展迷障。
我以为,新时代中国青年诗人要写出上好诗篇,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努力使得自己的写作变得开阔、开阔、再开阔些。
要有坚定的诗歌自信
新时代中国青年诗人与“诗歌前辈”相比,无论是所处时代环境,还是拥有诗学资源方面,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是好上加好的。他们应该更加沉着,更加自信,摆脱“被期待”状态。
中国,是世界第一大“诗歌体”。较为丰厚的物质条件和百年的诗学传统,成为新时代中国青年诗人思考与写作的逻辑起点。站在如此高的起点上,青年诗人应该满怀信心,轻装上阵,写出不亚于前辈诗人、同时还必须超越前辈诗人的诗歌佳作来。毕竟他们面对的百年新诗传统,远没有当年古体诗人面对唐宋诗词那么大的无法超越的极限压力。
新时代中国青年诗人比较理性。对于上一代诗人及其诗歌,他们没有像此前诗人那样采取激进的取而代之。反而,他们和上一代诗人之间亦师亦友,和平共处,各行其道。仿佛他们乐于被上一代诗人、前辈诗人期待着,写出让后者满意的作品。这就造成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诗人的时代焦灼。
为了急于交出答卷,写出让他人满意的作品,他们使自己的写作变成了一首首“练习曲”,宛如述川在《永恒的练习》里所写:松树“墨绿的针簇,/来回刺探着虚空”,做着“与季节无关”的、“恒久的孤独的运动”,丝毫感觉不到春天的生机。如此一来,诗人就成了莱明《造景师》里的“造景师”。他们刻意制造一些人为风景,使得诗成了“人造的假山”、“纸扎的花朵”。看上去很美,但终究不是真的山水和鲜艳的花朵。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诗歌责任、担当和作为,完全没有必要重复上一代人的老路,就像扶摇在《虚构》里所示:“万物各司其职/从不懂悲伤”。新时代中国青年诗人要努力摆脱上一代诗人的“阴影”,与他们若即若离,写出真正属于自己的诗歌,形成真正属于自己这个时代的诗风,最终为这个时代塑形雕像。
从安在《茫石贴》里说:“坐定,我也成为石头的一部分”,毕竟“石头是风最后的住址”。新时代中国青年诗人要形成专属自己这一代人的诗风,要成为专属这个时代的坚硬的诗歌石头。要形成有别于上一代诗人的、属于自己这一代“这一个”的诗歌特色和诗歌风格。
要有强烈的时代意识
诗人与时代的关系是既拥抱又克制的关系,如此方能避免机械的形式主义和低级的唯心主义。
新时代中国青年诗人要勇于面对自己身处的新时代。这个时代里发生的重大事件,即那些深刻影响历史发展进程的事件,如全球化、一带一路、脱贫攻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等,都应该成为新时代中国青年诗人写作的题材。
回望百年新诗史,上个世纪20年代,戴望舒和徐志摩等知识分子诗人写出了那个年代的时代苦闷;1930年代至1940年代,艾青和田间等抗战诗人写出了那个年代的时代强音;1980年代,青年诗人写出那个年代的“政治抒情诗”和呼吁新诗现代化的崇高诗篇。
眼下,“90后诗人”路攸宁在《归》里写道:“一言不发的是生活/滔滔不绝的仍是生活”。现实生活不是简单扁平的,而具有多种多样的形式和驳杂难辨的内容。比如,写家乡,既可以写记忆与当下纠缠的家乡,如刘文杰的《夏至书》:“白杨树目不转睛地站在村口/像守卫家园的战士”,也可以写文化变迁中的故乡,如树弦的《清明》所示:“在故乡与异域的距离里/在这个清明与下个清明悄悄交换时间的空隙里/我默默低头,仿佛一株株纤细的柳树”。
不知从何时开始,有的青年诗人故意回避“大现实”,转而倾心“小现实”,对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尤其是那些灰暗色调的细节念念不忘,像记流水账那样写些平淡无奇的“口水诗”。就像顾子溪在《像你在身边一样活着》最后所言:“所有你不在身边的日子被我写成流水故事/流水不腐/我欠你一生奔波劳碌、艰难险阻”。自然界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但如果把诗写成了流水账,那一定就会像泥沙那样被流年冲走。
诗恰恰需要写人一生中“艰难险阻”那样的“大现实”。不能全面、客观、真实地看待现实生活及其时代风貌,也是隐瞒和欺骗的另一种表现。对此,如李一诚在《说谎的安徒生》中所警示的:“现实是唯一的止痛药,却还需要忍受/强烈的副作用”。
我也不是说新时代中国青年诗人只能写“大现实”,不能写“小现实”;何况诗人们可以“以小见大”地、以写“小现实”为手段最终通达“大现实”。关键是,诗人们如何看待和处理“小现实”。如果故意避“大”取“小”、以“小”为“小”,而且是负性的、阴性的、扁平的“小”;这就成了大问题。这肯定不是新时代大多数中国青年的精神面貌。
令人欣喜的是,广大青年诗人,他们的诗歌作品满怀希望,如大树的《野竹林》所写:“我们忽然坚强起来,充满希望/仿佛一切磨难都走在变好的路上”;我们还能看到他们努力“焐暖岁月”(韩熠伟的《春天是一味疗伤的中草药》);更能看到他们积极进取,像胡游的《枇杷树》最后所写,“感谢这棵硕果累累的枇杷树/让我有了向上的冲动”。
新时代中国青年诗人要直面现实,既可以从正面直接“突入”现实,也可以从侧面走进现实,把“小现实”变成“大现实”,认清前者只是表达后者的手段而并非目的。
要有正确的价值取向
也许因为有些青年诗人对于世事茫然不争(公刘文西的《路中》),所以他们感觉“广场上的胜利贫乏无味”(阿海的《明天》),所以他们宁愿“选择中立”。在他们看来,选择“中立”,像“果子悬着”,“也只有悬着/才知自己的分量”(杜嘉俊的《苹果知道》)。但他们不知道:“中立”不等于“独立”,“悬置”不等于“个性”,“中立”和“悬置”并不意味着复杂。他们误把“中立”当“独立”,错将“悬置”当“个性”。我始终认为,真善美是青年诗人写作所追寻的正确的价值取向。早在抗战时期,艾青就出版了诗论集《诗论》。对诗与现实、诗与时代、诗与真善美等重大诗学命题就有很好的归结并进行了“新诗诗话”式的艺术表达。我觉得,艾青的这些话,不但没有过时,反而应该成为新时代中国诗人写作的诤言和良言。
诗人们不但要认识真善美,还要懂得欣赏它们,更要拿起笔来赞美它们。不同于穆旦写于抗战后期的《赞美》赞美“一个民族已经起来”,叶飚的《赞美》赞美的是九十年代的“辛劳和营养”、梦想和幸福,好让他的诗有个“尽善尽美的理由”。生活尽管复杂多样,但是通过经验、知识和思想,人们完全可以化繁为简,认识生活、把握生活和诗化生活。
要有大胆的创新精神
对于现代主义诗歌写作、后现代主义诗歌写作来讲,我们很有必要声明:诗歌写作要创新,不要“创恶”。
当然,创新,要“守正创新”。从某种意义上讲,创新有时候也是“创旧”。因为传统是我们创新的基础。所以,有人说,诗歌是发现,而非发明。数典忘祖,否定传统资源,只会使创新成为空中楼阁。黄雨陶在《三月十二日夜行道中遇雨》里说“杜甫太沉,李白太轻”,把“李杜”弃若敝屣,此乃写诗的歧路。
创新是一项系统的诗学工程。它要求新时代中国青年诗人要在思维、审美、语言和方式等方面进行全面的、有机的、有效的创新。比如,处于青春期的青年诗人,既写到了自己“体内的欣喜”(桴亘的《喜鹊》),也写到“父亲太极里方程”(桴亘的《我二十二》),同时还能写到老年人对故土的坚守(胡游的《老人的孝顺》),进而写到复杂生活和悖论诗学的“方法论”——“如果赶时间,就走最远的那条路”,“有秘密,就说给隔壁的耳朵听”(刘浪的《流水赋》)等等。此外,在诗体建设方面,新时代中国青年诗人,好像只擅长写短诗,而很少写长诗。
新时代中国青年诗人要想在世人面前展示自己的写作实力和魅力,光写短诗是不够的,还需要创作既有灵又有肉且还有经络的优秀长诗。
总之,新时代中国青年诗人要创新,既要力戒装神弄鬼的西方化的晦涩诗风,又要规避油腔滑调的本土化的口语诗风,不要盲目跟风赶潮,要有自己的定力和站位,努力形成纯正地道的属于自己这个时代的包容化诗风。
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导 杨四平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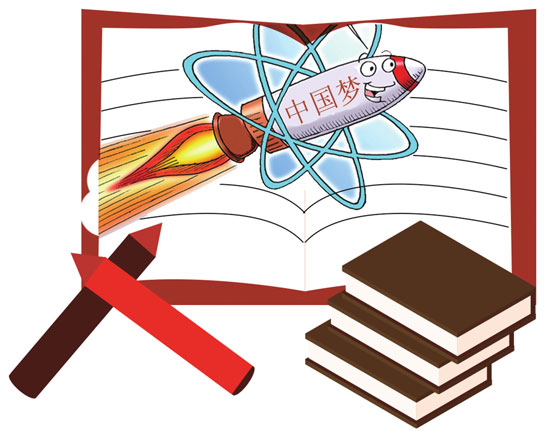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