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剑,男,汉族,云南昆明人。火箭军政治工作部文艺创作室原主任,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国家一级作家。先后出版“导弹系列”“西藏系列”的文学作品600万字,代表作有《大国长剑》《原子弹日记》《大国重器》《导弹旅长》《麦克马洪线》《东方哈达》《坛城》《祁连如梦》《经幡》等。
------------------
枪炮声常在徐剑的笔尖响起。
这位军旅作家个子不算高,说起话来儒雅随和,但是伏在一方书案前,他笔下的世界却足够恢弘壮阔。他写过早已远逝的战争,写过穿越世界屋脊的青藏铁路,写过“像雷霆一样沉默”的“天之骄子”战略导弹部队,也写过洪水、冰冻灾害之下人的渺小和顽强。
今年夏天,徐剑完成了历时两年采访、讴歌南海填岛劳动者事迹的《天风海雨》,为老英雄张富清写下《永远的军姿》。如今,他又投入到长篇报告文学《天晓1921》的采写中,寻觅党的“一大”代表的生命遗迹。
不到16岁参军,徐剑从一个导弹部队的工程兵、报道员、秘书,成长为一名军旅作家。从军中退休后,写过诸多重大工程、军旅史诗的徐剑说,他将转向作家个人叙事式写作。
9月3日,徐剑在北京宸冰书房接受了《中国青年作家报》“壮丽70年·红色传承”融媒报道小组的专访。
为什么不让这些战友走得热闹
七上八下。
这个再普通不过的成语,在徐剑眼里,是浸着血的。少年徐剑是一名为导弹筑巢的工程兵,他们的工作就是要掏空一座山,筑起一座城。遇到下雨,塌方时有发生,动辄损失一个排一个班。八个战士牺牲,七个负重伤,“七上八下”的特殊含义正是如此。
那个年代,一个导弹阵地被建成,旁边就会留下一个烈士陵园。每到晚点名的时候,那些牺牲战友的名字被叫到时,全体战士会一起大声答:“到!”
这些声音印在了徐剑心里。他常看到晚上七八点,警卫排扛着锹到烈士陵园里挖墓穴。他知道,又塌方了,晚上11点多,又有牺牲的战友要被埋葬,其中不乏跟他坐着同一节闷罐车来执行任务的战士。
他困惑地问,为什么不白天吹着唢呐放着鞭炮,让这些战友热热闹闹地走?
“你懂个球!”老团长听了这话,当即批评他,“当兵来这个小城,是为了让这保持和平和安宁。我们要是隔三岔五地抬着棺木到小城里绕一圈,这不是扰乱了小城的宁静?”
这一幕幕,让徐剑萌生了一个想法。他想为导弹工程兵的故事写一部书,写给那些甚至16岁就已壮烈在大山里的战友。
“他们的身体早已寂灭,英名应当留下。”徐剑说。写《鸟瞰地球》时,里面有50多个名字,是徐剑从烈士陵园里一个个抄出来的。
写完《大国长剑》《鸟瞰地球》之后,徐剑带着它们来到了烈士陵园。那天,乌云密布,没多久便大雨倾盆。他一直记得那一天。时隔多年,徐剑觉得,如果他的文学生命有缘起,大约就是从16岁那年晃了三天三夜的黑色闷罐车开始,从随时降临在身边的死亡开始。
“三不写”的规矩
写《经幡》之前,徐剑18次进藏。为了《麦克马洪线》,徐剑采访了8年。想去亲自看一眼战役旧址,徐剑还曾爬海拔近5000米的山,直至爬到心脏不适。而常爬那座山的战士说,他们扛一袋米上去,一半不能吃,“因为即便肩膀上隔着塑料布,淘洗再多次,那些米都还有汗臭味。”
“在多年的采访和写作中,我为自己定下‘三不写’的规矩:没有用脚走到的地方不写,没有亲耳听过的故事不写,没有亲眼看到的地方不写。”徐剑始终遵循着这个原则。
在很多采访中,别人会事前塞给他一大堆资料,但是徐剑不喜欢。“你给我的材料没有温度,没有血性,没有细节,让我自己谈。”有时从早到晚谈上十个多小时,能收获一两个好细节,徐剑也很满足。“一天有一个好细节,30天有30个,30个还不够构成你书中精彩的篇章吗?”不过,这与在选题上阅读大量背景资料并不矛盾。2002年,为了西藏选题,他返京时带走了32卷本的资料。
在徐剑的写作生涯里,这些精彩的故事是在日复一日的慢功夫中得来的。有一次,他跟许多记者一起去采访一位老军人。让他感到不能认同的是,有人才采访了半日,就提着资料满足地离开了。
但是徐剑也不为自己的努力自我感动。在《大国重器》讨论会上,徐剑怕与他相熟的作家、评论家不好意思指出他的不足,特意挑了几位30多岁的新锐评论家,请他们尽管提出作品的问题,不要一味说好话。
军旅生活为徐剑提供了最丰厚的土壤。导弹神秘、强烈,为其做出牺牲的官兵前赴后继,他们心中饱含为国为家的热血,以血肉拼搏着。这些故事里,宿命般的情节比影视剧更让人唏嘘。
一对小情侣相恋8年,约定那年国庆节结婚。结果时间到了,10月2日、3日、4日……那位战士都没有出现。一直到最后,女友等来的除了噩耗,什么都没有。在他们约定好的结婚之日前夕,她的未婚夫,一名导弹部队的工兵,挖长兵道时被砸,失去了生命。而那个年代,未婚夫墓地所属的陵园也是军事禁区,只有直系亲属才能进去看他。直到改革开放之后,这位”未婚妻”才带着丈夫和孩子,第一次站到了自己当年未婚夫的墓前。对于这位姑娘来说,当工兵离世的那一刻,她的爱就永远被一个死去的人带走了。
还有一位母亲,力主让孩子当兵,觉得“只有当兵才能完成对一个青年的塑造”。但是她的独子入伍3个月后就遭遇了塌方。当时反对孩子入伍的父亲,跟她离了婚。每到清明节,这位母亲就会到儿子当兵的地方,来看看自己唯一的孩子。
“这种故事太多太多。”徐剑写过磅礴的国家工程,写过无情的天灾,但是终究他要写的是一个个鲜活的人。他曾在《关于非虚构几个关键词的断想》中写道:
“文学就是人学,报告文学概莫能外,其文学的落点,必须对准人,对准那些创造了历史的底层小人物,对准那些改变了历史的大人物,但决不等于是表扬稿,小人物自有小人物挣扎的尊严、友情、爱情的温馨和人性的悲悯与感动。大人物自有大人物长袖广舞的从容、自信,以及时代漩涡之中的艰辛、艰难和悲哀、悲恸,甚至难言之隐。我写了30多年的报告文学,如果对于人的写作,可以概括一句干货,可以真刀真枪地操作,那就是报告文学对写人处理,应该遵循小人物伟人化、名人传奇化、大人物平民化。这是我多年报告文学写作的‘葵花宝典’,屡试皆爽,可以说放之非虚构领域而皆准。”
靠这样的写作观念、方法,《中国作家》原副主编萧立军评价徐剑的《东方哈达》时说,这本书“别开生面,文本创新意识极强,较好地解决了‘国家工程不好看,好人好事表扬稿’的问题,为国家重大工程的写作探出了新路。”
不要过多咀嚼个人的愁苦
有一次,一大批作家一起参访中科院,听科学家讲基因、超算、量子等前沿话题。但是徐剑发现,与大公司、科学家交流时,很多作家处于“无语”状,似乎没什么好奇的。
徐剑由此感叹,其实“每个人都在淘世相、情感、人生之井”。但是他很清楚地知道,这口井不管你淘多深,井口依旧是狭窄的。个人的体验诚然可贵,却无法代表一个时代和民族。
徐剑在多个场合屡次提到,深淘这几口井,“关键是要有一种精神的照亮,写出中国气派和风格的精神境界和海拔。我觉得当下文学写作,尤其是国家叙事和军队叙事,并不缺技巧、语言,甚至不缺生活和想象,最缺的是精神品质,缺的是一个作家在大时代之中的站位和姿势。我们将用什么思想和精神来展现新史诗?文学的最高精神品质是什么?就是思想的高度、广度和深度,通俗说,就是一种精神的海拔。”
想获得这种“海拔”,并非一日之功。三种“阅读”在徐剑看来非常重要。对书本的阅读自是其一。哲学、文学、历史等等,都该是作家的功课,一生都不该离开这些“思想的光芒”。其二便要“行走”。“读天下这本大书,”徐剑说,“每个人都是一本大书,都在展现一个世界。”而对天地的阅读是另一重境界。就如西藏的神山圣水,给予徐剑以精神的高度。
徐剑总觉得,“不要过多咀嚼个人的愁苦,要到老百姓中去” 。
他最推崇的作家是司马迁、杜甫和苏东坡。司马迁留下了不朽的场面和细节,用今日的话说,他是非虚构写作的巅峰式的人物。杜甫对苍生的悲悯情怀,使得一首古诗都能令徐剑泪流满面。而苏东坡人生坎坷,他能从苍生苦难之中体悟自己的痛苦,再达到一种更大的宗教境界。
徐剑不断提醒自己,对天地当敬畏,对苍生当悲悯,而不是将自己束缚在狭窄的一方天地里。
在他几十年的创作生涯中,手握鲁迅文学奖等30多项全国、全军文学奖。著作《大国长剑》《鸟瞰地球》《砺剑灞上》《麦克马洪线》《冰冷血热》《东方哈达》等,都在实践着他对自身“站位”的要求,锤炼锻造中国气派的能力。
徐剑的“变法”
作家的生命是双重的,他的生命本身,以及他的创作生命。16岁入伍,将徐剑从宿命般的绝望中拯救出来。当兵,被他当成一所“社会大学”。这是那个年代为数不多的改变命运的机会——原本徐剑会跟父辈、祖辈一样,面朝黄土背朝天,过着一眼望到头的日子。那不是他想要的。
徐剑一直感恩于他此生为之奋斗的事业。他能优雅地伏案写作,能挥洒创造力,这是很多职业不具备的幸运。但是这份“工作”没有看起来的那么轻巧。回顾21年前不惑的自己,徐剑还记得,当时他心中恐慌,总在自我拷问,“我怎么不断在生产文字垃圾?”
那时徐剑已获诸多大奖。当他到鲁迅文学院学习时,还有人说,你都可以当老师了,怎么还去当学生?
做出去鲁院学习的决定时,徐剑想的不是自己获得了多少荣誉。他觉得,自己是一个“野蛮生长”起来的作家,从没参加过正式的学习。他曾参加了北师大中文专业的自学考试,但是那点专业训练,在徐剑看来实在是不够提。
徐剑乐于与骄矜保持足够的距离。1998年,徐剑进入中国作协。有朋友说,你怎么这么骄傲,迟迟才来入会。徐剑心里却觉得,自己拿了很多奖,但是进入作协,自己还不够格。“现在很多人才写了一本书就急不可耐。”这让徐剑感到无法认同。
前往鲁院学习,是因为徐剑当时很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文学生命遇到了坎儿。那4个月的作家班经历里,有的是为扩展人脉而来,有的是为发表作品而来,徐剑做了减法。他没着急去找什么人出书,只是安安静静地读书,鲁院的“气场”和文化资源让他受到了滋养。
这份滋养很快帮助徐剑成熟和突破。自那以后,徐剑每本书的结构都不同。在文本的突破之外,徐剑还去古典文学中寻找坐标。他不断探寻最中国化的文字,让自己的笔逐渐被养得洗练、干净。还有人用“雅正之美”来形容他后来的作品。
如今,花甲之年、已然退休的徐剑在进行自己的“衰年变法”。“人生最大的敌人是你自己。”徐剑笑着说,“要截断一些诱惑。”
穿军装的44年,徐剑说自己“问心无愧、无悔、无怨”。军队叙事、国家叙事、重大工程叙事,他做了20余年,颇有成就。而今,他想转向有作家独特立场、个性化的私人叙事,写出一部让自己足以“带去见马克思”的作品。
(感谢宸冰书房提供采访支持)
本报记者 胡宁 只恒文 赵小萱 视频 岳琦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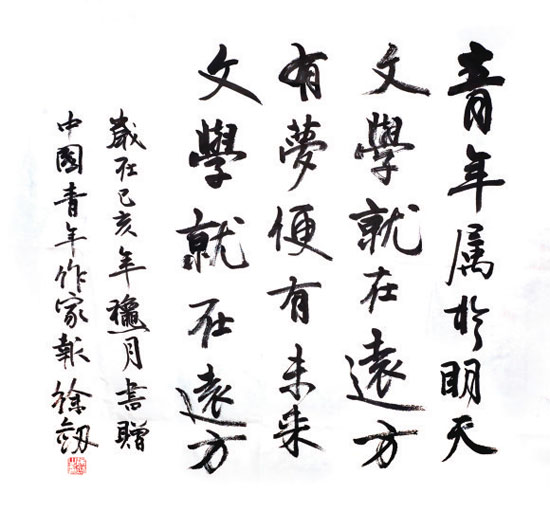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