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倚翠染红的山中,林木秀丽,无限风光。
山中人朴实劳作,一年四季,才得些许收获。土不养田,山不养人,轻壮的年轻人,荷包缚裹,踏进远方城中,誓不再归还。根在土中不能稍动,叶能随风,飘向四方。那老幼之辈,力也不济,为山所困,再不能登高临望,只能想象着远方。
粮谷之物不丰,果桃却因地制宜,到处都是。每到采买之季,久不闻人语的山中,也是十分热闹。老幼结群,挎篮提包,上树摘果,下地捡桃。装的稳实,剔了残坏果子,尽捡好的放推车上。沿着山路,顺着古道,送到山下采买场中,按斤结价,付钱收货。
这钱该怎么用,村长自有吩咐。给村里两位老师置办衣服,不能再穿土布衣服了。
话是这么说来的。这村被裹在山里,进不得,出不得,不尴不尬的。闲人谁曾来这,敢是二三百年都不见外人。村里人丁不旺,百年来也不过百十户。外人来这里,也着实是“没前途”。也并非真没外人,“好女子不嫁山里汉,好汉子要娶外头女”,也有些山外女人嫁进来,没几年也就都偷跑了。
要说是“外人”,也还真有。不过,说是外人,其实是亲人。早年这里还有私塾,后来建了小学。学校不大,几间瓦房,大门也只是拼了两扇门板。有几个老师,熬了几年,打实里待不下去,走了。村里人拦他们,求他们,盼他们,终究还是离去了。孩子断了书读,老人也都泪眼无奈。
直到12年前,初春。
一对新婚夫妇到这旅游,都是十足的“驴友”。贪恋着山间风景,晚了时间,迷却方向,跌跌撞撞走进村子。女孩还扭伤了腿,男子背着她敲开村户的门。没有驱逐,没有嫌弃,没有要钱。安排热饭,熬下草药,收拾空铺。将歇了几日要走,为表感激,夫妻许诺明年还来,给村人带些外边的新鲜物件。
村户也只是淡淡应着:“还来个什么,都想着出去哩。”
女子问道:“这么好的山,还出去吗?”
村户说:“这里要真是好,那些先生们也不会走,娃儿也不会断了读书,怎么能寻个出路。窝山里头一辈子,算个甚么出息!”
叹着,望着,追忆着。夫妇问起缘由,知道学校空了的事。巧的是二人都是教师,听了这话,都琢磨起来。
临到快走时,说道:“娃儿的书不会断,俺俩个都是教师,俺来这教书!”村户们能信?这地方,谁稀得来?不愁鸟儿飞出去,只愁狐狸进来也迷路。这话他们这么一说,村户这么一听,也就罢了。谁能跟他们认真?
料是谁也想不到,没人跟他们较真,自个却跟自个较真。两口子还真来了,带着行李,扛着书籍,清扫学校,就此在这安家。吃不惯的土饭,也吃惯了;受不了的山雨,也受得了;记不清的山路,也记清了。就此,学校也新了,娃儿们也多了,也有读书声了。
这两口子,可就苦了。饭不精细,磨坏肠胃也得吃;房不牢固,补补也得去住。至于衣服,除了自个带来的,再没穿过新衣,都是土布麻布,村户织剪送过去的。这一教,就是12年。
对于两口子来说,还是教书,还是生活,还是园丁般劳作。三尺讲台,一根教鞭,半支粉笔,就是12年岁月的定格。对于村户们来说,那是破天荒的12年,娃儿们又读上书了,能走出去了,能过上山外的生活了。夫妇最早的学生,也已经大学毕业了。
不知道外人有没有说这两位傻,为其感到不值,大好年华浪费了。村里人也是无限的感恩与惭愧。而他们却不以为然,他们看来,这是他们的本分,也是他们最理想的生活。这12年的支教,就是12年的守望。守望了山里人的梦,守护了娃儿们的未来。只是要守望的这座山,不光要12年,要守望到300年。他们也有子,有子就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尽也。他们就是要“愚公守山”,不肯轻易弃之。子孙都要守望这座山,不许山里断了教育。
平凡的生活,能活出不一样的平凡。而平凡的守望,就是守望不一样的平凡。
谢同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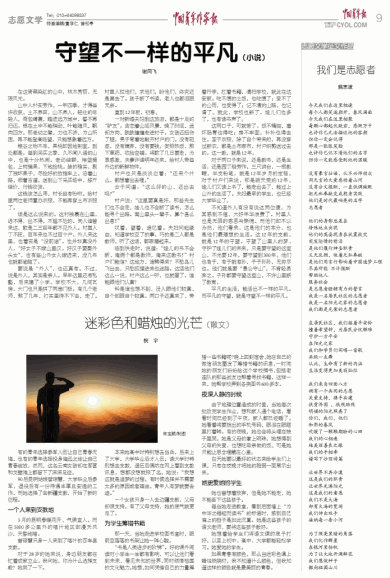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