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春天,疫情情绪断断续续,好在有两位朋友的好书陪我度过:女作家林雪儿记录脱贫攻坚的长篇《北京到马边有多远》,张生全反映乡村振兴的长篇《重返蜀山》。
优秀的作家总是在挑战惯性
四川小说一直有个优良传统:乡村叙事或者叫乡村图景书写。早期沙汀和李劼人,到改革开放初期的周克芹,再到后来的嘉陵江、大巴山作家群,叙事脉络,一直很清晰。乡村早不是那乡村,作家换了一茬茬,可总觉得里面隐含某种绵延不断的东西,似乎挺强大。
就说近两年。阿来《云中记》写了一名祭师与一个随山体滑落的藏族村庄,小说明确地打上了四川乡村与藏民族文化两条烙印。马平的《高腔》从题目、题材,甚至文本,哪个方面看都是典型的本土书写。乐山周恺的《苔》土腔土调讲述晚清乡村和小城的迭部,离乡村更近,距城市稍远。大凉山阿薇木依萝的《蚁人》写农村人进城各种不适,貌似异化的乡村叙事。
乐山的林雪儿和眉山的张生全呢,几乎同时推出乡村题材,或非偶然。
张生全几年前一连搞了好几部历史题材。以洪雅柳江为背景的《最后的士绅家族》定位明确,也最为成功。三年前,张生全说,不再写过去了,尝试一下当下,特别提到要写一座蜀山。我就想,他要寄托的蜀山是哪一座呢?岷山?峨眉山?青城山?大雪山?还是他的家山瓦屋?
林雪儿据说也在孕育一部超越个人医者经验的当下题材。林雪儿是妇科医生。《妇科医生》和《亲爱的宝贝》受到读者欢迎,除了驾轻就熟的女性心理和视觉,还有妇科医生天然的善良与悲悯,以及对生活、生命和人生,超出一般人的铭心刻骨。我手写我心的林雪儿,很大程度体现了作家的动机态度与作家情感的表里一致性,这令我敬佩。闭关两年,远离职业背景打造的全新力作,还能带给我一贯的美好吗?
叙述惯性,是双刃剑。事实上,一段时间以来我就怀疑他俩是不是有点冒险。都说扬长避短,他俩为何反其道而行之?尽管有疑问,可我还是保持了期待,因为我相信他俩对于文本的掌控能力,能支持叙述的变数。优秀的作家总是在挑战惯性,求证陌生的路上。
山有多高,村有多远
我几乎是同时拿到《北京到马边有多远》和《重返蜀山》的。担心纯属多余:张生全的那座山,就不是“一座山”;林雪儿的未知领域,却是一个明确的乡村。绕了一圈,他俩在题材开拓上的华丽转身——原来不约而同又回到四川作家的叙事轨道上来——那蜀山的山高,与马边的村远。
山有多高,村有多远。这是一个审美的互文话题。一边是诗意栖居,一边是落后闭塞,形而上与原生态,接纳与拒绝,逃离与被逃离,所有以矛盾综合体为张力的乡村叙事审美,从上世纪开始就已被本土前辈们翻来覆去嚼了不知多少遍。可以说,林雪儿和张生全正在干的,可能是件吃力不讨好的活路。二十一世纪的乡村叙事,又如何在现代性语境下,尝试撑破审美疲劳的天花板,演绎一番与世纪变革同频共振的新时代和弦?
马边我没去过。我的马边,完全来源于林雪儿的经验:它在乌蒙山区的大风顶。大风顶很大,草木葱郁。一群祖祖辈辈土生土长的彝族同胞,赖以栖居。它叫雪鹤村,离北京不仅仅是距离上的偏远,还贫穷,落后。当然那里的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大块吃肉,大碗喝酒,说话做事大大咧咧,善良的善良,耍脾气的耍脾气,一个个乐天派。
张生全并没有交待笔下蜀山的出处,但从他的讲述来看,他对那座山那群人再熟悉不过。各种家族恩怨和世情瓜葛,扯不断,理还乱。老的不开化,认死理,年轻的,一厢情愿,想跟别人划清界限。男男女女,有钱没钱,都有血有肉,不遮遮掩掩,敢爱敢恨。那一幕幕,爱也不是,恨也不是,熟悉而又陌生。
最关键的一点,两个乡村的老百姓,都在干同样的大事,脱贫攻坚或叫乡村振兴,以图改变乡村的日常困境和人情窘态。
当然,这是宏大的也是时髦的主题。如此,问题也来了。两位作家似乎都面临同样的叙事障碍:如何规避表面的主题热闹和叙事雷同,深入乡村的那些鲜活细部,除了讲述什么,呈现什么,传说什么,展开什么,还要像神经末梢一样,更深入地触摸那山那草木,那村那群人的集体意识,感知他们的共同情感和温度。也就是说,作家能不能完全把自己的认知和情感盲区给屏蔽掉,然后一头扎进去,像有机细胞一样,与那里的山水草木同呼吸,与那里的父老乡亲共命运,最后完成两处描写对象与一致文化意义的转型演绎和反哺性倾诉,这不仅仅是创作的态度问题,更是个审美的技术活。
显然,张生全和林雪儿都很好地做到了。他俩的写作经验,从来就没有离开过那山那草木,那村那群人。张生全和林雪儿,都在农村出生长大,后来客居他乡小城。多年的笔下实践,散文的抒写也好,小说的固化也好,多是变换形式的个人经验,去见证改革开放以来,四川城乡的历次巨变。无论乡村忆旧,历史感怀,还是现代经验,无非文本递进,叙事伦理那么清晰地自在——曾经的“乡村”,诚实的也是善良的叙事。这也是我说的,他俩很好地继承了四川作家传统的意思。
但是,他俩笔下的乡村又那么地不同——
蜀山,那文化的山高:海拔的“高”,还具生生不息的神性(母性)的意义。那里的人天然地与外界有着某种不信任甚至对抗,他们机智地与城里人周旋,因为他们为了守护祖祖辈辈的大山崇拜,不想按照别人的想法去改变既定的习惯和日常。也许,他们是错的,不合时宜的,但他们毕竟努力过,挣扎过,像中国乡村版的堂吉诃德,可这不就是自己乡下一些亲人么?
马边,那诗意的村远:地理的“远”,被主人公的情怀缩短到了三棵树——那叫核桃、柏树和栎子树的三棵大树,还有一本叫《万物的签名》的书,一段叫远方的审美空间(距离美)。脱贫攻坚当然不是诗人写写诗那么畅快,也不是修条路,集中搬迁,发展核桃、茶叶,搞几个项目,处理些乡村干部小腐败等那么简单。主人公从北京来到这里,实际上就已经把自己当成一棵草木种了下去,不仅是种在地理的那一段远方,也是种在情感的那一片近里。于是,那村那人,与那山那草木,一样焕发生机。
显然,他俩的乡村审美,不可替代。比如,林雪儿真情洋溢,引领我们“对自然和人性温暖的向往”(阿来);张生全冷静诚实,“并没有贸然地给出乡村振兴的答案”(阿来)。再如,张生全把众多的人物放在圆心事件中,让他们放纵性情,自由倾述,由挖掘人物多变的内情,表现乡村问题的纵深;林雪儿更擅长让人物随个性心理的线性流淌,在更开阔的城乡空间和叙述视野中,成长丰富,揭示命运。又如,林雪儿的行文不疾不徐,并不拘泥于在特型细节上用力,而是一点一点在人与自然的对话中,编织主人公的日常美好情绪,文笔致敬周克勤;张生全坚持一贯的戏剧性场景营造,如文学评论家陈思和所说,以“嘲讽悲悯的笔触写世态”,又颇有沙汀遗风。
《重返蜀山》有很多有趣的人物,喜旺、唐朗、严庄、邓娟、黄昌婆、觉英、李师公、马月英、李秉、施西西等。他们各自代表一种不可或缺的底层姿态,共同营造了蜀山的生态群落。有了他们,蜀山丰富而生动。张生全在刻画他们的时候,固然有着多年乡村生活不可磨灭的原型记忆,但张生全拒绝了模式化,更拒绝同质化,目的就是要雕塑一群乡村英雄的个个不同。他们是作家的父母兄弟,乡里乡亲,也是读者记忆的唤醒与共鸣。他们是作家流向各个方向的泪点,最终汇聚成多声部的情感之瀑,在小说的结尾突破我们的心堤,一涌而下。
《北京到马边有多远》的主人公林修,更是理想化的个人英雄。他是小说的男一号,始终占据着作家笔下的C位。第一书记林修是虚拟的英雄形象,但他与林雪儿在体验生活时挖掘的那些个原型,又是高度重叠的。林雪儿一直在寻找一个有诗意有情怀,与自己的人生理想契合的小说人设。她去马边采访扶贫干部,整理纪实稿子时,她发现这个人设天然地存在。他阳光智慧,诚实善良,爱憎分明,身体力行,眉间有星空,胸中有家国。他是作家日常审美的那一个(他),更是每一个我们集体理想的同一个(他们)。他或者他们的事迹会让你鼻子发酸,让你看到平凡中的不平凡。他或者他们最大限度地消弭了日常审美的琐碎,在主人公、作家和读者之间,无缝构建了感动与被感动的多向网络,也留下了现实冲动与叙述呼应的典型个案。
当前,正值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统筹衔接的关键时期,需要自上而下的关切与自下而上的共鸣形成有效合力,也包括文学讲述的用力。作为一项全新的文学命题,它的宏大和难度,超越了作家既有的写作经验,也将极大地挑战作家关于现实丰富的捕捉与历史深广的洞察能力。这个时代强烈地呼唤优秀文学的典型与完整性的表达,如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所说,“这一非常迫切且鲜明的‘应做之事’,说起来是容易的,实际上做到是非常非常难的。”
文学的应有之义
越是广阔和陌生的,越是未知和可能的。越是挑战的,越是文学的应有之义。作为基层作家,张生全和林雪儿的直面和担当,难能可贵。他俩选择了中国乡村的细胞——那山那草木,那村那人,以它们为叙事之本体,深情地去仰望,小心地去解剖,勇敢地去塑造,最后为我们徐徐展开了一幅忐忑不安,丰富生动,又富有文化内涵和诗意温暖,值得感动值得期待的审美画卷——
林雪儿,自由地倾述了个人英雄塑造的快感;张生全,没有回避基层干部群众集体觉悟的复杂性。
林雪儿,塑造了一个面对他们,从来没想过站在自己的立场去改变别的,而是只想着感化什么的林修;张生全,刻画了一群面对自己,一次次突围,又一次次被等待救赎与自我救赎的彷徨和矛盾沦陷的英雄。
林雪儿,几乎唯美的纪实,最大限度模拟了生活的真实和温暖;张生全,矫健敏锐的笔触,提示还应关注那容易被忽视的尊严。
他俩的乡村其实都是进行式的,也是互补的。
不管是理想主义,还是悲观主义,他俩都寄托了自己的文学追求。
作者简介:
沈荣均,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思想及文艺史随笔作家。现居四川眉山。
责任编辑:只恒文
沈荣均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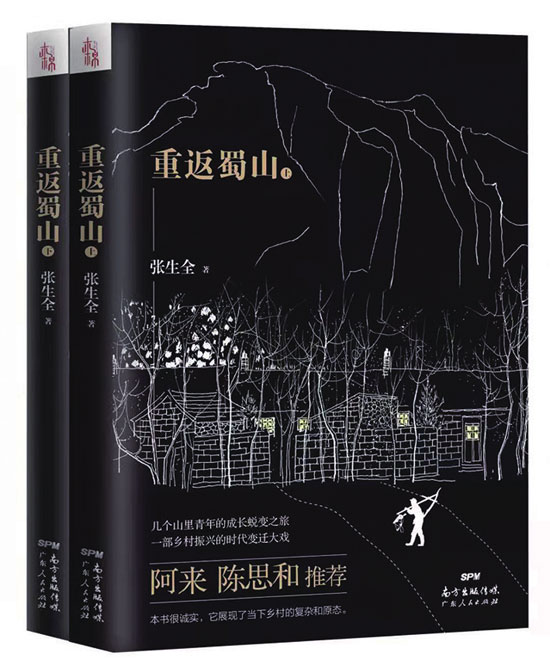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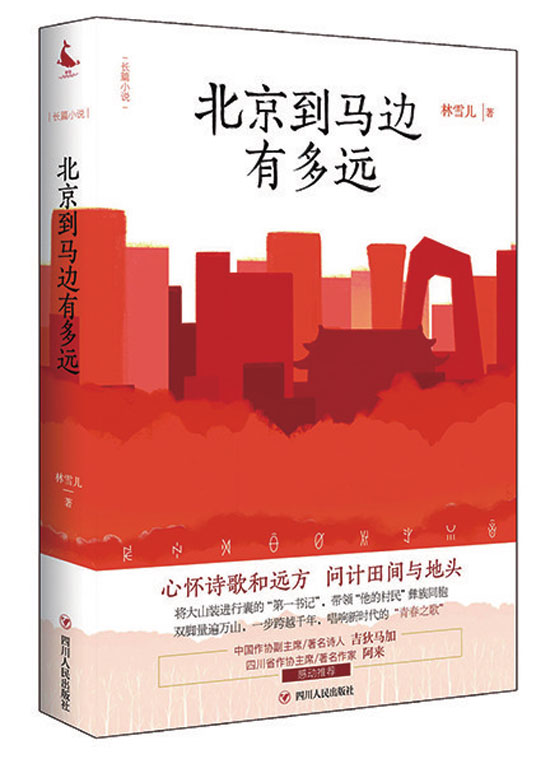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