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子里很乱,外祖父佝偻着身子来回踱着,一只手插在老旧的军大衣兜里,仰着头,时而喃喃自语。他将大衣裹了裹,低下头,半埋进衣领里,挡住逸出的那点儿光,而进入我眼帘的,是那道在夕阳下若隐若现的,来自外祖父的光,那是什么呢?
外祖母出殡那天,我母亲和三位姨妈凑了点儿钱置办酒席,招待前来吊唁的亲戚朋友们。因为有雨,所以我父亲和几位姨父一合计,干脆在院里支个塑料棚,门口两桌,院里四桌。在熟悉的土灶旁,母亲面色凝重地倒米,添柴,含着米香的蒸汽弥漫在整个厨房。我没见外祖父的身影,问母亲,母亲说外祖父上山了。
刚下过雨,山路湿湿滑滑,我猫着腰小心翼翼地往山上走。稀松的林木映着一片片裸露的岩石,在一块平坦的空地旁,外祖父靠着树,望着山下的老屋怔怔出神。我张张嘴,没有出声。只见,外祖父轻叹一口气,慢慢从怀里摸出一个看上去已有些年头的麻布包,颤巍巍地解开绳带,用手里的棉布轻柔地擦拭。随着太阳逐渐高升,我有些沉不住气了,凑过去叫了声外公。那时,我才大致看清,外祖父手里细细爱抚的,短短的,有些扎眼的物件,原来是一杆旱烟枪。
外祖父和外祖母生在有山有水的地方,对着青山,长在天门河河畔,老屋百十步处便是两亩瓜田。春夏之际,外祖父种瓜卖瓜,外祖母织衣做饭,而母亲和她的姐妹们在田间玩累了,便会以瓜填嘴,各种香软滋味都能尝个遍。若是到了冬季,河里结了冰,外祖父便会用祖传的法子在河面砸开几个窟窿,用捕来的鱼维持一家人生计。那时候,繁星满天,空气中含着一丝丝花香,天门河两岸绿树成荫,潺潺河水夹着桃花柳叶,像极了他们后来岁月流逝的模样。只是,在有了我母亲十多年后,外祖母渐渐变得有些神志不清,连吃饭也离不开外祖父。天门河河岸的花开了又谢,谢了又开,外祖父原本笔直的腰杆也在日复一日的辛劳中变得弯曲。地里的瓜,我尝着,总觉得味道复杂。
回城当天,外祖父有些失落地站在一旁,躬下身,从怀里摸出小布包,摊开,捻了捻手指,沉声说:“杆断了,拿去接接吧。”
我一愣,从他手中接过布包,端详起断成两截的烟杆。烟杆摸上去有一种铜的质感,通体雕着花,头部半截镶着一小颗一小颗绿色的宝石,而尾部半截的木制托柄则被磨得发亮,靠近烟嘴的地方还用红线挂着一个小荷包,上面绣着字,背面缝上了一张泛黄的黑白照片。照片里有一男一女站在河岸上,男青年虽穿着一身老式棉衣,但掩不住他眼角眉梢处的英气,而女青年则紧紧挨着那个男青年,甜甜地笑着,怀里抱着一个露出烟锅的袋子,身后便是芦苇丛生的天门河。
等我拿着布包准备上车时,外祖父突然沙哑着声音对我说:“要常回来看看啊。”说罢,蓦地从我手中夺过小布包,靠在胸口,脸上似在挣扎。最终,外祖父叹了口气,又重重地将小布包放到我手心里。车在不断往前走,外祖父的身影逐渐缩成了一个小黑点,我心想,一定要尽快再回来一趟。
可是,三个月后,我却不得不回去了。又是似曾相识的场景,坟前,树影斑驳,随意散落的阳光顺着风亲吻着每个人的脸,不远处的青山沉默着,一如往常。
去年暑假回家,我坐车经过青山,夕阳卧在山尖,山脚下,一幢幢新房拔地而起,那一瞬间,在车窗后,我看着不远处的青山,又想起了我的外祖父,想起了他们那个逐渐远去的时代。
责任编辑:龚蓉梅
杭州师范大学钱江学院2019级学生 闵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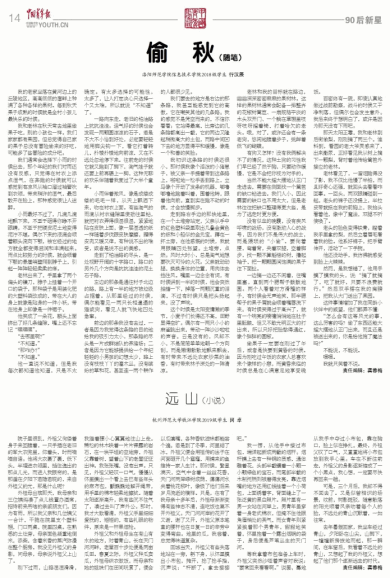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