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孝纪《故园农事》显示了一种强大的生命力,也构成了湘南乡村精神范本的力量。在我看来,黄孝纪近年来特别努力,所有的作品文字都十分朴素。为什么黄孝纪能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出版那么多的作品集,从他的作品中不难发现,他写自己的生活经历,所处的生活状态给了他丰富的创作积累,在一般作家发表都困难的前提下,他以蓬勃的力量书写了乡土散文写作的先锋气势,让人值得研究与探讨。
全景性、史诗性和开放性为一体的讴歌
《故园农事》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书写一个阶段的湘南乡村史。这一个阶段刚好截取上世纪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之间的时间段。在此期间,中国发生了农业集体解散,分田到户,再到农民工进城三个历史事件。由此所及,农村的生产生活方式,农民生产的积极性,田土山水的生态环境演变等急剧变化,给他的书写给予了多角度的解剖。从农事的角度,回顾那段真实的历史生活,还原湘南农耕文明到后工业文明的思想脉络。
黄孝纪的故乡八公分村,典型的湘南小山村,至今都没有较多的工业交集。与桂阳县、郴县三县交界,一条没有名字的小河,穿村而过。村里至今还保留着许多原生态的生活生产方式,包括耕种,包括养育,包括农业取向,以及日出而作日落而归的生活状态。在他的笔下,每一篇文字都非常明显保留了千百年的农耕传统,和农耕文明。黄孝纪的《故园农事》分了六个章节,分别是种田、作土、育山、养殖、手艺、农闲。这六个章节中,有一个总的特点,那就是把湘南乡村历史命运个体化,把个体命运历史化,由此形成一个横纵交错的骨架,使之带有全景性、史诗性和开放性的讴歌。
所谓历史命运个体化,个体命运历史化,直白点说,就是作家通过自身的生活经历,把时代的责任感,融于作品中,再通过种田、作土、育山、养殖、手艺等生活场景,让时代变化在湘南一个偏僻山村的微不足道的农业叙事中,激起思想的波澜。这种波澜,亦是湘南乡土文化的三层皮,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正是有了这种哲学形态上的思想美学,他的作品写作动机,不仅是从琐碎的个人生活经历来延伸,更是对乡村历史发展的潮流不断提升、总结与凝练。
黄孝纪讲述的是1970年到1999年这30年间的故事,也是八公分村的农业生活史。在第一节中,杀叶积肥,犁田耕作,种秧莳田,看水杀虫,双抢交公粮,种烟分田,突出从集体农业到分田单干这一时期的生活经历。实际上作者所表达的远不止是这些,他把笔伸向中国农业发展和改革发展史上更为宏大的画面,非常广阔的思想。说明它不仅要表现历史交替时期具体的变动和是非,而且要大力表现在湘南乡土和沧桑岁月中,普通农业劳动者的真诚与勤劳,坚韧与追求。这就使读者既可看30年的日常生活场景,同时不断地把自己加入进来,在作品里找到自己,激发心灵追求的向度。黄孝纪与我年龄相近,从他的日常生活中,这种叙事立意的维度,恰恰契合了我们共同的思想汇集——在最平凡的湘南生活画面里,隐藏着动人的诗意和丰沛的社会内容和社会意义,这正好是这部作品集的美学意义。
以平凡的表述打动读者的秘密所在
黄孝纪的叙述,依旧是平坦的方式,这种写作的概括方式上,形成了自己的写作特色。我们通常在讨论乡土文学作品的审美内核和审美灵魂,以及其精神内涵这一个维度上时,会发现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很多出色的作家都会用平凡的表述,来打动千万读者的内心。越是平坦的,愈发激起读者内心的共鸣。
《故园农事》有三种思想上的“交叉”——农业集体解散与分田到户的交叉,分田到户与农民工进城的交叉,再到进城创业与归乡反哺的交叉。这三种交叉既是平行线,又在过程中产生思想和灵魂的共振或交集。因此,我敢判断,黄孝纪写的不是纯粹的,完全封闭的八公分村,他重点书写的也是思想与灵魂深处的追问。在笔者看来,黄孝纪内心深处期望的故乡,既是封闭的又是开放的,既是包容的又是情感的寄托,最能代表中国底层命运对美好生活更大的期待。作者年少时从省城读书分配,再到市里做记者,如今到长江三角洲开启新的奋斗历程,他的笔触无非是想通过自己的命运,把命运的交错,与生活关系和八公分村的变化紧密联系,使得乡土文化更富有思想的张力。当然,其中也不无作者对未来更美好乡村建设和乡村发展,寄语自己的心愿和理想。
《故园农事》第二章作土系列中的烧火淤、挖土、种豆、栽瓜、灌园、割杂粮、砍苎麻、扯花生、挖红薯、莳冬菜,讲的都是地里的活,我也有亲身经历和体会。无论是从文本的结构还是故事的本身,其视觉已经深入湘南乡土生活的本质。当时,湘南农村并不富裕,仅仅是衣食自足而已。乡亲们大部分都是物质上的贫穷者,可文字里我们可以阅读出,这些朴素的乡亲都有高贵的精神,他们活得自在,满足,快乐,坚韧,顽强。劳动者的笔下,本身就蕴含了丰富的精神厚望。他们对命运的不争,不屈,力图通过劳动改变现状的强烈愿望是值得敬重,值得书写的。这里也有读者作者自己的影子,既有着传统的守道之美,也有着对苦难的敬仰之心,更有美好未来的向往之情。像一股强大的激流,激荡着湘南人民的奋发之心。
在第三章中,垦山、摘油茶、打桐子、捡柴、守山、摘山苍子、背杉树、挖锰石、采草药等,这里开始显现出八公分村的村民对美好生活更高的期待。这些文字,把八公分村人崇尚美好,崇尚幸福,崇尚劳动致富的精神特质,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长幼有序,仁厚孝悌,勤俭持家的伦理秩序和伦理精神,以传统美德作为精神的底盘,如厚土般稳定。这些故事,彰显了劳动者的人性美和人情美。作家路遥认为,“人生充满了苦难,在与其不断的搏击中,人才会活得充实一些,才能获得幸福感”。作者借故园农事,把苦难的书写和在苦难中的经历,升华成意识上的思想美感。
还原生活的向度,让幸福唱响厚土
黄孝纪确实让读者对其故乡八公分村心生敬畏。因为他的内心没有掺杂任何功利成分。超越于苦难,超越于门庭和乡土伦理的秩序。乡土写作的内核主要还是“真、善、美”,这是《故园农事》写作中道德理想观的基本构成要素。这样的爱,源于内心的修养,以及对故园的爱恋。特别在今天,社会浮躁,人心浮躁,热爱故乡更显得奢侈与高贵。在第四章的养殖篇中,放牛、养猪、养狗、养兔、养猫、养鸡、养鸭、养鱼、养蜂,把个体命运与众生命运的完美结合。于是,从伦理上讲,这些家禽走兽,都是我们共生的依赖。
在第五章中,讲述的是湘南老手艺,比如做木工、做油漆、打铁、补锅、补鞋、弹棉被、织毛衣、做媒、剃头等等,我们有可能会提出,黄孝纪的作品无限地放大生活的苦难,完全失去了文本的诗意。然而,这是一把双刃剑,既有尊重的一面,也有寄托的一面。这也是个体意识觉醒和自我实现的未来之美,激发青年一代尊敬历史,尊敬乡土,尊敬奋斗。
在第六章中,讲述的是农闲时节。比如修水库、装电、做砖瓦、烧窑、建房、赶圩、讲古、看电影、放爆竹,回过头来看,也正是有了这些生活闲话,才会有了作者对农村生活方式和传统土地观念的期望。与其说,这像黄孝纪个体命运的一部精神史,还不如说是一部宏大的湘南农村精神史,更是一部中国农村的精神史。黄孝纪写的是八公分村的人与故事,发掘了个体意识,更为生活在这块厚土上的人给予厚望。
黄孝纪通过文字讲述故乡,赞赏故乡、理解故乡,甚至是拥抱故乡的坚忍、温厚、善良,博大。另一方面,作者身上又有叛逆的、不安分的东西,那就是现代个体意识的萌动,就是要改变命运,走向未来,扬弃父辈们的生活老路。一边固守乡土,一边赋能乡土,一边尊重传统,一边摒弃传统,这种矛盾的理念,一直在作者的脑海中,在内心觉醒般的进行自我对话与呼唤。这种沉重的意识与开放的理念,被不断变化的生活向度所糅合。这种自我矛盾与悖论,恰恰带来了作品上荡气回肠般的撞击。
行文至此,我们现在应该能够理解,黄孝纪的乡土散文及《故园农事》为什么能深受读者喜爱。对于一切试图改变现状,改变命运的人来说,人生必然会有一场奋斗,不仅需要心灵的抚慰,精神的超越,道德的提升,骨子里更需要不屈的信念。每个人的人生道路不必高大,但必须高尚。在他笔下的故园,既卑微又骄傲,既平凡又矛盾的往事,能给青年一代以沉思鼓舞,给奋斗者以精神的滋养,让美好的故园赋予更新的,向上的生命力。从而成就了其作品的湘南乡土文化的范本,凸显其独特的审美地位和当下意义。
责任编辑:只恒文
谭旭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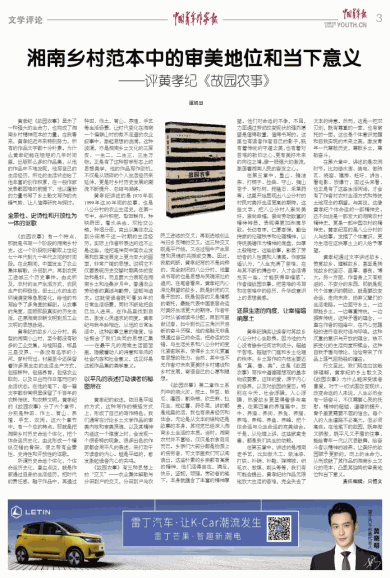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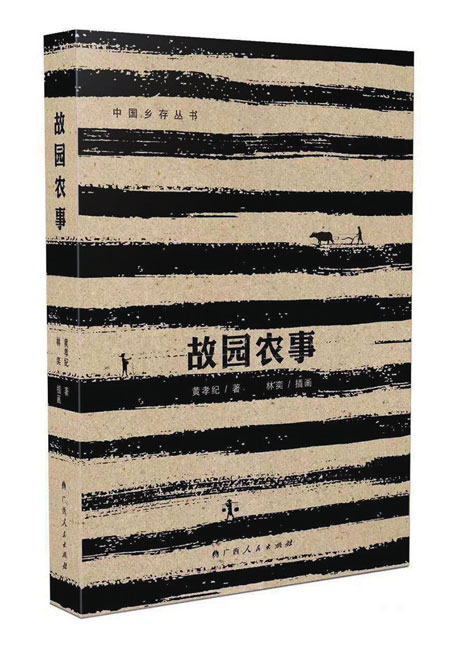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