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末
翻开《摆渡人》的时候,正是暮色四合时,夜色沿着远山曼延,抹去白昼最后的痕迹。那一天我开始倾听迪伦,勾画这个姑娘的样子,还有她所见的山川与河流,荒原与陡坡。
合上《摆渡人》的时候,正是晨雾弥漫时,清爽跨窗而来,万物初醒,晨光绚丽。那些关于迪伦的故事在那一天浓缩起来。回过头看,迪伦她不再单薄,不再简简单单的是那个角落里被排挤的姑娘,她的故事不是遇到崔斯坦一见钟情的俗套,也不是仅仅勇敢穿越荒原回到人间的冒险故事。
她孤独却充盈,她渺小不起眼,却坦荡宽广。她的样子,没有得天独厚,没有与生俱来,她就像是千千万万个普普通通的小孩子,你看得到她的那些可贵,看得到她的隐忍和辛苦,看得到她澄澈美好的心。但你不会感到同情,因为你会可贵她经历过那些残忍和冷漠,让她成为她。
你见证她那两场“渡”的痕迹,便懂得她的勇敢,她的诚挚与渴望。这一条跨越生死的列车,她没有见到抛弃她的父亲,也没有如期美丽俏皮的出现在父亲面前,列车停下的那些时光,她做了梦,跨越了一条孤独的河流,她遇到了崔斯坦,接受了摆渡,给予了摆渡。她摆去了过往的冰冷与灰暗,渡来了恒久的爱和希望,而崔斯坦,这个看上去并没有构成摆渡的角色,却也在无形中摆去了冷漠和千篇一律,渡来了有温度的灵魂和人间感知。
痕迹
八月长安在《你好,旧时光》书中借着余周周的口吻讲道,“每个人总有一个时刻,觉得全世界为自己做了一次配角”。关于这个世界的幸运,我们总会讲到“主角光环”。拥有高光的那个人,我们称之为主角。成为主角也许并不是每一个生命初来乍到便与生俱来的期望,但是它却是每个生命个体最共同的特征。我们希望获得认可,得到赞许,拥有陪伴,感受珍贵的爱,在所有有教导意义与陪伴意义的故事中,好像都只有主角才会拥有这些美好。
而迪伦却与传统定义中的主角背道而驰,它恰恰是最不完美的主角。她很孤独,她的成长满是辛苦和隐忍。她没有长在阳光下,没有恰到好处的友谊,所有令她感到快乐的东西都是短暂的,总会戛然而止。
被欺凌和被抛弃是她整个生活的琐碎痕迹,不顺心好像才是她生活的主旋律。她穿着看起来破旧突兀的衣裳,固执地搭起生活的屏障,屏障外面是那些孤僻怪异的定义,她在屏障里面演绎着自己的主角生活,建立自己的城堡。在已然七零八碎的生活里,陌生又遥远的父亲仿佛是她去屏障外面过上新生活的唯一救赎通道。父亲陌生但是却仍为父亲,血缘关系下,很多柔软和依靠便肆意生长。迪伦开始准备,与其说是准备,倒不如说是冒险,用自己的满腔勇敢寻找新生活的入场券。
在故事的人物设定中,迪伦足够卑微了。她身上的痕迹,无一不是黑暗的映像,但是,当迪伦开始小跑着奔向寻找父亲的旅途,每一帧关于她的画面,你会发现每一个黑暗映像背后的闪光点,足够耀眼,足够高昂,足够刷新那些黑暗的映像。
迪伦会遇到崔斯坦,也会感知死亡,但你没有读出过她的恐慌。她靠着小小的一双手,亲自为自己蒙上了屏障,保护自己真诚的心,维护自己小孩子的清澈与美好。所以即使荒原孤独,恶魔成群,象征着温暖安逸的小屋总离她那么远,她也从未感到惧怕。她从未期待过环境,也从没对环境抱有过期望,她的屏障从不因环境发生变化,她从没因为哭得过糖果,她少之又少的糖果全都是自己寻觅到的。
所以,她表面上那些卑微惨淡的痕迹背后,是一个茁壮成长的灵魂,有力量去与环境抗衡,有底气与环境握手言和,有勇气与周遭宣战,也能坦坦荡荡地接纳。
我总会在看到关于崔斯坦独白时热泪盈眶。这个从没拥有过选择权的生命总让人同情和感动。关于选择权的问题,是很多期望终结的第一原因,也是很多遗憾产生的源头。没能选择人生的起点,没能拥有选择自己何时长大的机会……作家路遥在《平凡的世界》中借孙少平写到这样一句话,“我认为,每个人都有一个觉醒期,但觉醒的早晚决定个人的命运。”这句话一直在我脑袋里,在每一个回想起那些与美好背道而驰的经历时给予我陪伴。
所以啊,世界上有这么多人,但却没有两个人完全一样,这是因为那些别具一格的痕迹,才是我们存在的意义。可能有一天我们都会明白,如果生命是一条孤独的河流,我们渡来的,往往是带着我们痕迹的,我们拥有的这一只摆渡船,也是烙着我们印记的船只。这个世界有很多条河流,我们各占一条,各掌舵一只船只,船只破旧与否皆无妨,旅途的崎岖或平坦,且看掌舵人。
摆渡人
书的扉页写着,如果生命是一条孤独的河流,谁会是你灵魂的摆渡人?
摆渡,如果细想这两个字,不免会抛出疑问,摆渡,是要摆去什么,又要渡来什么,一摆一渡之间,跨越了什么。
问到这里,我们的心底便有了关于摆渡人的答案。也许我们才二十岁,刚刚拥有了对生活的理解和生命意义的感知,但是细细回想孩提至今的回忆,那些最幸福和最苦涩的记忆一定是放在秘密宝库的最底层,那些记忆你很少拿出来与他人分享,所以啊,能决定摆去什么,渡来什么的只有你自己。这一摆一渡之间,跨越的便是你自己的那条生命长河。
回到书的扉页,如果生命是一条孤独的长河,谁会是你的摆渡人?如果生命是一条孤独的长河,只有你才是真正的摆渡人。
责任编辑:龚蓉梅
西安理工大学学生 王好雯(20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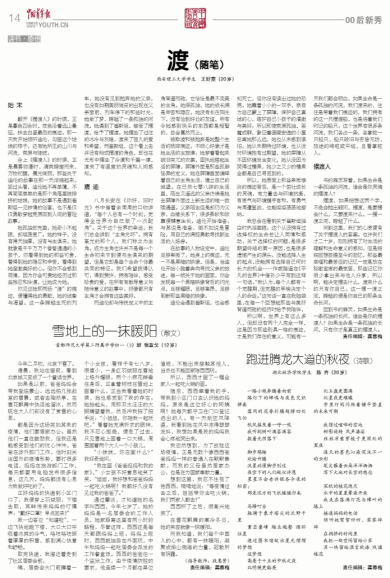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