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数我生命里那些重要的日子,2018年12月25日,是不能忽略的一串数字:不是因为那天恰逢圣诞节,而是因为它是《中国青年作家报》创刊的日子。
彼时的我,刚刚从纸媒行业黯然离场,转投进互联网行业的大门,犹记得当天,最吸引我眼球的,是底下的一条评论:“在纸媒不景气的当下,中国青年报社逆流而上,创办了《中国青年作家报》。是从容赴死?还是涅槃重生?或许都有可能。”
其实在我的心里,也有着同样的困惑。但文学自来就是一种予人希望的东西,我还是怀揣着姑且一试的火种,投向她。
很快,时间就给出了答案。2019年2月26日,我的《蜀乡薯香》刊发了!报纸到手还需要一段时间,但我已迫不及待,便厚着脸皮向编辑讨要了一张版面的照片作为纪念。捧着照片,我把那张印着自己名字的铅字作品,细细地品读了一遍又一遍:文字被编辑修改后,成熟了很多,像一个不修边幅的男子,被由里及外地进行了打理修饰,透着一股迎面而来的干爽凝练,也透着编辑老师字斟句酌的用心。
收到样刊的当天,我曾写下一段文字:“如果生活像一种毒药,那么文字,也许是一种解药;毒药难免会痛入膏肓,却不料解药也会让人上瘾。感谢《中国青年作家报》的垂青,让孟春时节更添一梦呓;也让一自困之人,耕垦一丝坚定。”
从此,周二就变成了一个值得期待的符号,因为那是《中国青年作家报》的出版日。很多周二的早晨我起床第一件事,便是打开中国青年报App,查看当日的报纸是否出炉,以便第一手品尝新鲜。每次在《中国青年作家报》上看到自己的文章,眼神相撞的瞬间,逐字逐句的记忆回溯,文字河流里迸发的喜悦,足以治愈眼前的愁绪万千。
通过编辑老师们不懈鼓舞和个人坚持,我也逐渐开始在其他刊物上崭露头角,像第一次登陆《中国青年作家报》那样,把自己的名字变成一个有象征意义的铅字。我觉得《中国青年作家报》就像我们的家,每写成一篇新稿,第一时间我会想投她适不适合;被多家刊物婉拒后,我会转头“回家”诉苦和寻求帮助。家总是一个不常回但习惯性会第一时间想念的地方,她总是鼓励我们以梦为马,勇闯天涯。
保持热爱,青年可期!未来无数个100期,我们还要在一起。
本版责任编辑:龚蓉梅
重庆新媒体编辑 谭鑫(27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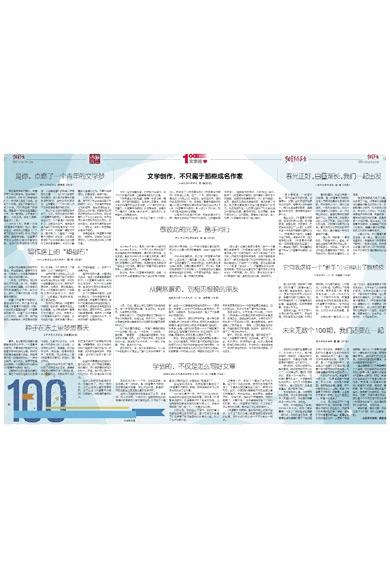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