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年前,我的父母从贵州前往广东打拼,为广东的建设发展贡献自己的青春。二十多年后,我从广东出发回到贵州,回到我的家乡——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在我的家乡,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和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们一起做着一件有意义的事儿,这就是我最大的“心安”之处。
——题记
在这样浪漫的地方
到达贵州的时候正值盛夏八月。
贵州的天空时常都是澄净的蓝天,阳光也更加热烈,但整体的气温要比广东更适宜,反而不会觉得闷热。从贵阳北站出发前往册亨县,到达册亨一中已经是暮色四合的时候了。
我到现在仍清晰地记得,那晚的天空很干净,漫天繁星,晚风清凉,温柔地抚去了最初的不安与紧张。
册亨一中就坐落于群山之间,四面翠峰环抱,个别日子早起时就能看到缥渺的云雾流连于山顶,宛若仙境。
一道从山间蜿蜒而下的溪流,将学校的教学区和生活区分隔开来。夏天的时候溪流湍急,冲刷着两岸的沿堤,每天早晨的闹铃就是这清脆的水声;冬日反而愈发温柔,水流清澈得能看到溪底石头间的小鱼。偶尔还会看见附近村民家雪白的大白鹅在溪流上觅食,水花溅起时还会在阳光的照耀下反射出七彩的虹光。
一座石桥和一座吊桥连接了溪边两岸,老师和学生们每天都在岸边孔子像的注目下走过大桥,人声喧闹时桥边盈动的是最生动和青春的活力。
我就是在这样浪漫的地方,开始了我为期一年的西部支教生活,开始了这一段今生难忘,也为之自豪一辈子的奇妙旅程。
西部支教是吾梦
没想到,我最终以这种方式回到了贵州。
二十多年前,我的父母从贵州前往广东打拼,为广东的建设发展贡献自己的青春。二十多年后,我从广东出发回到贵州,回到我的家乡——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扶贫先扶志”,我以一名青年志愿者的身份,以一名册亨县第一高级中学英语老师的角色,参与到了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伟大事业当中,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算参与了自己家乡的建设和发展吧。
“去西部支教”,这一个念头起源于大二升大三的那个暑假。那时候我和小伙伴们一起组队参加学校组织的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赴广东省惠州市博罗县大坑小学。大坑学校老师严重不足,现有的老师平时只能给孩子们上语数英等主科,其余的科目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于是我们就为那里的孩子提供第二课堂教学、教育关怀服务和心理健康服务。在这15天里,在惠州博罗的山里面,我清晰地意识到,在广东尚且还有教育如此落后的地方,遑论贵州等欠发达省份。这一次的“短期支教”极大地影响了我,在某种程度上也改变了我对自己人生的规划,“去西部支教”就成了我大学后半段努力的方向。有时候缘分就是如此巧妙,这一次和我一起参加研究生支教团计划,来到册亨一中支教的小伙伴当中,其中有一位就和我一起参加了大二暑假的那一次“三下乡”。缘分让我们再一次携手同行。
大二的时候,我曾惊叹于一位师姐的情怀与抱负:“这世间的一切,都与我有关。”后来她继续升学,投身于我国扶贫政策的研究当中。
大三的时候,我也聆听过一位结束支教返回校园的师姐的动人分享:“我的支教梦,在西部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在我的人生里永远闪耀。”
在我选择成为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成为一名支教老师的道路上,我其实是受到了很多优秀的人影响。他们满溢着家国情怀,他们有着新时代青年的蓬勃活力与澎湃力量,我是由衷钦佩和羡慕的,我希望自己能够和他们一样,为贡献一些自己微末但踏实的力量。
在我的家乡,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和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们一起做着一件有意义的事儿,这就是我最大的“心安”之处。
我成了一名英语老师
刚到达册亨一中,我便立刻面临一个挑战——我竟成了一名英语老师。
册亨一中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教师人才紧缺和学科结构失衡,特别是英语学科,高一年级还有好几个班的英语课程没老师承担。我因为大学英语六级的外语水平,最终被学校安排到了英语科组,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我本科专业并不是外语,最担心的莫过于上不好课,耽误了学生们的未来。为了尽快熟悉英语这门学科,每堂课我都需要大量时间打磨,一堂45分钟的课程,我要花几倍的时间去设计教学过程和制作课件。
这里的学生英语基础普遍不好,个别学生只认识26个英文字母,连最基本的音标都不认识。有的学生内心是抵触英语的,认为不管怎么学都学不懂,索性就放弃不学了。
说实话,刚开始的适应期其实挺焦虑的,课上得也很吃力,最初的教学效果还不尽如人意。但现在我回想起来,反而觉得这也是我学习的一个过程,自己在这个阶段自学也学到了很多,以前没留意或者忽略掉的知识点都慢慢补了回来,因而感到特别有成就感。举个例子,为了让学生学会拼读单词,我要求他们掌握好音标,但让人无奈的是,因为多年不曾复习,我竟发现我自己都不太记得个别音标的读法了,关于“爆破音”和“摩擦音”的发音方法也忘得差不多了,为此我只能先自学网上的音标课程,请教大学里英语专业的同学和朋友,重新掌握音标的知识点。
我与他们之间的关系也不再只是师生关系那么简单,而是——互相成就,共同成长。
我见证着他们的风华正茂,而他们也映衬着我的成长。
我越来越能明白,当老师的快乐其实很简单,就是看到学生们能不断进步,掌握越来越多的知识点。我有一个班,上学期第一次月考英语成绩年级倒数,但在后来的几次月考中,每次都进步了一点,进步的不多,但我依然很高兴,反而觉得更踏实。期末的最后一堂课,我问他们,这学期的英语课,大家最高兴的事儿是什么?有的同学说是给他们播放英语电影,有的同学说是学唱英语歌曲,但其中有一个答案我听得很清楚:“我会拼英语单词了!”那一刻心中的欣喜,我至今难忘。
纸上得来终觉浅
除了上课外,我还和小伙伴们一起,各自兼任了一个班级的副班主任,参与班级管理。
我曾送过生病的学生去医院。
我曾为学生的成绩而操心。
我曾和许多学生谈心谈话,尝试给出自己的建议。
我曾为如何教育犯错的学生而纠结万分。
在过去的半年当中,我经历了很多以前从未经历过甚至从未想象过的事,这都真切地告诉我,当一名老师并不容易,当一名好老师更难。
在教学推进的过程当中,我发现学生们非常缺乏关于理想信念的教育,并不知道自己为何读书,为谁读书,对于未来也是迷茫不清的,个别学生有时候甚至会因为成绩的一时落后而自责焦虑与自我否定。
于是我和小伙伴们一起,利用“副班主任”这一平台,首次创立了“青春正能量”宣讲团,利用班会课和晚间课余时间,围绕“社会时政、青年心理健康、梦想奋斗、理想信念”等主题,结合自身经历与故事,为册亨一中的学生们进行主题宣讲与系列分享,力图打破以往班会课单向传送“枯燥说教”的“旧印象”,树立双向互动“活泼有趣”的“新风气”,谨此希望为大山里的他们打开一丝关于外面世界的缝隙,让他们产生好奇心。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当你身处其中,才能感同身受。以前的我对东西部教育不平衡只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认识,并没有什么切身的体会。但来到册亨一中之后,随着工作的渐次铺开,我才对贵州省,特别是偏远地区的教育事业发展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我国东西部教育资源不平衡的关键不在资金不平衡,也不在教学设备不均衡,其核心矛盾在“人才”,在教师资源的不平衡,就是缺老师,缺好老师,教师的学科结构严重失衡。因为各方面社会资源或个人发展的原因,许多优秀老师“进不来”,部分老师“流出去”,造成了巨大的教师人才缺口,这或许也是我们这些服务于基础教育的志愿者来到这里最大的意义。
你的职责是平整土地
校内的基础教育是我们的主责主业,但同时我们也尝试走出校园,走入社区,走进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服务。贵州省是易地扶贫搬迁大省,册亨县也是一个深度贫困县,易地扶贫搬迁之后的后扶工作任务仍然艰巨,如何做好脱贫攻坚后扶工作、减少返贫现象发生的可能,打破贫困的代际传递,是我们当前需要思考和努力的方向。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我们需要努力的地方还有很多,需要去做的事还有很多。但我相信,只要我们一件一件事扎扎实实地去完成,在党和人民需要的地方踏踏实实地做、撸起袖子加油干,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在祖国西部的大地上留下属于我们的痕迹!
“艰苦奋斗、严谨治学、求实创新、为人师表”是华南师范大学的校训,大学四年里,我在无数的场合中聆听了无数次,最初我对它的认识也仅仅局限于“校训”,但当我站在讲台上,面对着上百追求着知识与智慧的明眸时,我才真正明白它的意义。
余世存先生在《时间之书》中有那么一句话,我将它记在我的笔记本扉页上,每一次翻开笔记本的时候都会瞥到:
“年轻人,你的职责是平整土地,而非焦虑时光。你做三四月的事,在八九月自有答案。”
谨此共勉。
特邀编辑:董学仁
华南师范大学研究生支教团 邓文杰(23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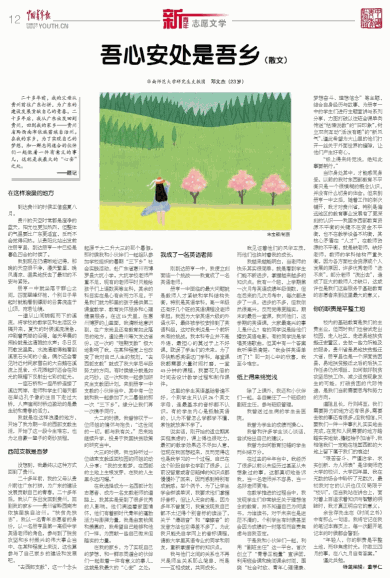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