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祖列宗在上,今有陈家家主陈秉生教子无方,即日起,卸去族长一位,陈家幼子陈小幺逐出家门,族中除名。”陈家家主跪在蒲团上,磕完头,拿起管家递的香插入香炉。
陈氏族人一片哗然,陈二叔作为族中老人,重重地咳,示意族人安静,朝陈秉生虚福了一礼:“族长啊,幺儿还小,你这不是断了孩子生路吗?”陈秉生咳了咳,面色发白,灰色长袍褶皱。一向得体,最重衣冠的族长,今日如此狼狈。他心中也难以割舍陈家小幺,只是“不得与戏子为伍”的族训不可违。定了定神,陈秉生握紧拳头抵在唇间说:“二叔,他是我儿,我亦不舍,只是他顽劣不堪,我亦心痛。”还未说完就背过身,快速擦着眼角。祠堂大门大开,灰色的衣襟单薄,风一吹,摇摇晃晃,一步两步,步步发虚。
陈小幺躺在暖阁里,心里盘算着老头儿什么时候放他出去找宋玉,想想那矜贵的人儿,浑身不得劲。曾经高门大户,宾客盈门的宋家,如今竟是这般光景,小妾当家,正室的儿子被卖去戏院,也不知道那个憨货吃了多少苦,曾经多爱笑,一口一个小幺哥,现在……
“哐嘡。”门被大力推开,陈小幺看着威严的小老头儿,身上有难掩的疲惫,实在不忍心气他,拉着他的手说:“老头儿,宋玉你也知道啊,他不……”陈秉生打断他的话,强硬地说:“祖宗之法不可违,你若不管他,你还是你的陈家小幺。”陈小幺生气了,瞪着大大的眼睛,不可置信地问:“爹,你在开玩笑吧,宋玉如今落难了,也不知道他受了多少苦,我要去救他。”陈秉生被气笑了,挽起袖子上前扇了一巴掌:“小幺儿,你可真行,你以为你算什么东西。打赏得多、包场,就是去救宋玉?滚出去,从今天起,我没有你这个儿子。”陈小幺捂着脸,头也不回地离开了陈家大院,躲在拐角处,看到大门紧闭后,对着那个方向,磕了三个头,擦掉眼泪。
陈小幺带着买的烧鸡去找宋玉,看到他躺在精致的拔步床上,手握着一本书,颔首低眉慢慢翻着,仿佛还是十年前的宋家少爷。陈小幺走过去,抢过他的书,拉着他下床,收拾出他的餐具摆放整齐。宋玉有一搭没一搭地吃着,随意问道:“陈少,今日来得好早,新学会了《长生殿》可要听一曲?”陈小幺笑着说:“宋玉,你明知道,我不是为了这才来找你,我只是想关心你。”
宋玉手一僵,鸡腿掉到地上,染上灰尘,脏得让人没有食欲。宋玉笑着指着掉落的鸡腿,“陈少你看,我像不像它,让人恶心。”然后随手一扫,瓷器破碎的声音刺耳。宋玉双手双腿并用爬上床,被子里传出呜呜咽咽的声音。
等再出来的时候,他抽出枕边的书:“我每日自省,我到底是谁,是冠满苏州的宋家大少,还是艳满戏院的玉哥儿。我自三岁起,提笔练字,寒来暑往,祖父夸我字清隽有力,力透纸背,将来大有可为。我饱读诗书,我是宋清隽啊,我不是什么玉哥儿。”陈小幺站在原地,想过去抱抱宋玉,但还是合上了门,出去买了宋玉喜欢吃的蟹黄酥,外加一盏冰饮。
等他回来的时候,打眼一瞧,又是那个面若桃李、矜贵风逸的宋清隽。陈小幺把东西递给宋玉,宋玉打开一闻,舒服地闭上眼,“这是城东第二家的蟹黄酥,挺远的,你倒是有心,记得我喜欢这种玩意儿。”陈小幺呲了一声:“我想不记得都难,是谁小时候说认识路,带着我从城南跑到城北都没找到。没想到吧,结果在城东,让我白挨了一顿打,想不记得都难呐。”宋玉白了那人一眼,让滚,陈小幺卷吧卷吧衣袖,可怜兮兮地说:“宋玉啊,我如今无家可归了,老头儿气性大,不要我了。”宋玉叹了叹气,终是无奈地点了点头,递给他一串钥匙:“这是戏园附近的院子,这些年攒的好不容易买的,给我养老用的,仔细着点,弄坏了你赔我。”
夜深,陈小幺攥着钥匙去找住处,被陈家管家拦住,递给他一个包裹,还有一封信。走进房门点开灯,看落款是母亲,大致意思是,给带了钱,省着点花,和老头儿正在吵架,不答应她就回娘家。陈小幺追上去让管家转告母亲,说自己一切安好,别和老头儿吵架,儿一定拼出一番事业,光耀门楣……
“哼,还光耀门楣,就他?夫人啊,给小幺的钱带够没,我仔细看了看,那处地方不错,没有苦了那个崽子,就别分房睡了。”陈夫人回应的是一声关门声,一夜无话。
陈小幺路过园子,听到里面咿咿呀呀地唱着:“半行字是薄命的碑碣,一抔土是断肠墓穴,再无人过荒凉野。”婉转千回,男子独特的嗓音,却赋予了独特的故事,像是讲述战场无人生还,姑娘容颜不再,等一不归人,让人不禁泪目。陈小幺看着梨花树下身姿绰约的宋玉,还是掉头就走了,他大概不想被人看到。陈小幺听人说过,男子身形不够柔软,唱不了戏的就喂药,挨饿,鞭打,那样清清贵贵的人,怎能让人看到衣冠下遍体伤痕呢?玉哥儿可能需要,但宋清隽宋玉不需要,他只想全了自己的衣冠。
1937年淞沪会战后,苏州城人人自危,戏园生意倒是红火。宋清隽告诉陈小幺:“你看台下那些人,成天点什么《望乡》《牡丹亭》《浣纱记》,让戏子在台上唱着,仿佛他们一喝彩,就上阵杀敌了。我要是能出了戏园子,我一定去当兵,上战场杀他个人仰马翻,酣畅淋漓,不枉此生,活个畅快。在这精致的戏服下,我活得不人不鬼。哎,小幺哥你觉得呢?”陈小幺被宋玉眼底的光迷住了,这样的宋玉不再精致,却鲜活、有血、有肉、有人气儿了。陈小幺忙不迭地说:“等陈家一族搬走,我们就去当兵,你文绉绉的,还是给我当军师吧。我这些年跟着商队走南闯北,也没白混,拳脚功夫相当了得,护你一个书生崽还是稳稳的。”宋玉发出来会心的笑容,陈小幺拍他脑袋,大笑懂不懂,你这样怎么开心得起来啊?宋玉不管不顾了,跟着这个浑人大笑起来,哈哈哈哈哈,嬉笑声冲出了这四角小院……
陈秉生带着族人上香叩拜祖宗,那年卸去族长之位后,竟无人再揽,竞相推辞之下,陈秉生继续担任族长。站在最前面,陈秉生悲怆地说:“族人们,如今国将不国,族将散族,我们陈氏一族在此几百年,现在活着的可以走,但我们的祖先呢,他们长眠地下,要跟着我们逃亡吗?”族人们或小声哭泣,或看向祠堂,或抱成一团,在这一片低沉中,有汉子出声:“族长,我愿请战,以血肉之躯护祖宗安宁。”
一石激起千层浪,请愿声层出不穷,陈秉生看向这些熟悉的族人,心中悲鸣,高声振臂:“族人们,我陈秉生不是贪生怕死之辈,我愿同诸君共死,马革裹尸全了一场忠义。只是你看看他们,族中稚子何辜,我们不能让他们在还不懂生死的年龄,死得不明不白。带着孩子们走吧,留下我们陈氏一族的根儿,就先这样吧……”
陈小幺回到陈家大院,看到父亲在和母亲争执,父亲支使丫鬟收拾行囊,送母亲回娘家。母亲全然不顾形象和父亲吵:“怎么一个个都送走,你好一个人去拼命啊,我就是要在这,为你留盏灯。你和别人拼命的时候好留点心,别死心眼,一味去送死。”父亲安抚母亲:“小婉,你不要如此固执,还是走吧,就听我一次吧,下辈子,我还下聘。”母亲哭哭啼啼不依不饶,陈小幺不合时宜敲了敲门,跪下行礼:“儿不孝,在外几年,未能尽孝,请父亲母亲先行,儿子定会护族中安然。”陈秉生笑着看着这个逆光的少年,满满地遗憾:“幺儿,父亲这些年时常在想,我那时那样专断,是不是错了啊?”陈小幺笑了笑,未尽之言,不言而喻。陈秉生气得踢了他一脚,时隔几年,三人终是抱在一起,那个怀抱真的很幸福,后来陈家幺儿时常在梦中忆起,醒后泪湿满巾。
母亲被父亲一碗蒙汗药送上马车,家中丫鬟仆人跟随,走得很匆忙。父亲常常在族中开会,安排人手,打探消息。外面炮火连天,每日有伤亡消息,城内人心惶惶,戏园人走茶凉,戏子们各奔生路。看着这四方院,宋玉没想到出来得这么容易。这么戏剧,乱世之中竟是我宋清隽的活路啊!
城破了,宋玉被人流裹挟着前进,躲在破庙里,听着外面马蹄声、汽车声、整齐的步伐声。宋玉和一群人在破庙过了一晚,天亮后,阳光很强,目光所及之处,刺眼的红。宋玉看到满地尸体,血染了一地,扶着墙吐到不能再吐,扶着墙越过一具一具尸体。很久很久,浓稠的血沾满鞋底、衣摆,能闻到令人作呕的浓稠的铁锈味。
靠着仅有的意志力,最后在陈家祠堂找到了陈小幺,陈小幺被人打晕藏在散乱的牌位后面。陈小幺问宋玉:“外面现在怎么样?我爹呢?”宋玉坐在地上双目无神,任陈小幺怎么问都不回答。陈小幺跑出去,抹着眼泪,扇了自己一巴掌。蠢死了,中了老头儿的道,端来最爱喝的排骨汤,味道不对以为是老头儿手艺退步,全然没想到啊,蒙汗药,老头手段真低,但……老头你别死啊。
陈小幺跑着,被尸体绊着摔了一跤又一跤,爬起来继续找,双目通红。宋玉找到陈小幺的时候,陈小幺正抱着陈秉生回到陈家大院,偌大的院子,只有父子两人。收敛衣物的时候发现一封绝笔:“吾陈秉生率全族青壮年奋死抵抗,但奈何长矛大刀不抵长枪短炮,以一换五终是勉强,我族中之人,纵然身死,亦不妄生。”在白色的里衣上,用血写成的,歪歪扭扭,锵然凄惨,陈秉生是书法大家啊,他的绝笔……
陈小幺将父亲埋在他早前规划好的风水宝地里,其实就是环山绕水。陈小幺看向宋玉,扯着一抹笑问:“宋玉,我要去当兵,你还去吗?”宋玉捶了他一拳:“说什么呢?我可是你的军师,你个大头兵还不得靠我。”落日的余晖拉长少年的身影……
责任编辑:曹竞 毕若旭
晋中信息学院学生 贺豆(21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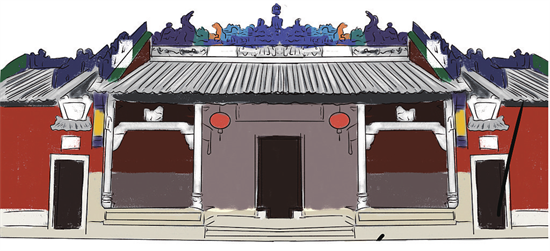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