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坚守写作,从少年开始,写到离世,他能一直保持敏锐性和洞察力吗?或者让这问题简化一点,一个人的文学创造力能保持多久?
写作者关心这样的事情。
几乎没有谁,不想让文学创造力强大和长久,有生之年,永不枯竭。这是不是奢望,只在幻象之中?
诗人米沃什,把这个幻象变成了现实场景。1980年,他69岁,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接着又写了20多年,写出不少杰作,至少再出版了5本诗集。他活到了90多岁,也写到了90多岁,这不是件容易的事。
这次读诗,读米沃什,读他几首短诗。你可以把这些诗看成一些刻度,它组成的那把尺子,也许能用来测量,我们自己有没有文学创造力,能不能长久保鲜。
米沃什写过一首《偶遇》,全诗很短,还不到10行:
我们驾着马车,穿过黎明时的冰冻原野。
红色的翅膀自黑暗中升起。
突然一只野兔从路上跑过。
我们中的一个用手指点着它。
已经很久了。今天没有谁活着,
那只野兔,那个做手势的人。
哦,我的爱人,他们在哪里,他们将去哪里?
那挥动的手,一连串动作,砂石的沙沙声。
我询问,不是由于悲伤,而是感到惶然。
写这首诗的时候,米沃什25岁,总是心事重重或心不在焉,容易感伤外界刺激,以悲观态度评价生活。这与世界大战阴影越来越浓密有关,与他的国家波兰已经承受、即将承受的太多磨难有关。初读这首诗,我有些不解,米沃什那么年轻,怎能遇到野兔和车上同伴都已死去的“已经很久了”的事情?想了一想,才想到米沃什的现实观:对现实的拥抱,要有距离才能做到,要升飞到现实上空才能做到。于是,他年轻时的“偶遇”,可以发生在多年以后,是他提前看到了一切。
有了米沃什面对现实的这种态度,年轻诗人也能思接千载,视通万里,无拘又无束,自在又自如。
你能看到他/它,只因为你想看到他/它。
继续来读米沃什。
有一首《为我的八十八岁生日而作》,看题目像是他晚年的作品。
一个城市,簇拥着有顶的通道,狭窄,
小广场,拱廊,
向下伸入海湾的台地。
我被年轻的美女俘获,
我的肉体,并非经久不衰,
它在远古石头间起舞。
夏日衣裙的色彩,
数世纪老的小巷里拖鞋后跟的轻击声,
给予我们关于永恒复归的感官享乐。
很久以前,我忘记了,
参观大教堂和加固的塔楼。
我就像一个单纯地看着而不是擦身而过的人,
一种崇高的精神蔑视着他那灰色的脑袋和痛苦的年纪。
被他的惊异拯救,永恒而神圣。
这首诗让我想起,有一次面对访谈,米沃什说:“尽管我年纪很大,但我一直都处在非常年轻的状态中,漫游不休,并且总是惊奇、困惑。”不经意中,他可能说出了他的秘密,想要文学创造力与个人的生命一样长久,需要完成这几件事:有年轻心态,不停地漫游,时常会困惑,总遇到惊奇。
那个年纪的人,心动于年轻美女,他此时的状态是真年轻。但在整体看来,已经有了岁月的痕迹。诗人活得够久了,经历了苦难之后、悲壮之后、辉煌之后,到了可以随意、可以不在乎、可以很通透的时候,他在语言背后也有勇气和自信,思考自己以前没有想到的事物,描述自己仍在写作和生活之中的现场感。
还有一首诗,写了他晚年的成熟,从语感上看可能写得更晚。
临近九十岁那年,
一扇门才在体内打开,我进入
清晨的明澈。
往昔的生活,伴随着忧伤,
渐次离去,犹如船只。
而我笔下的国家、城市、庭园、海湾
离我更近了,
等待我更完美的描述。
我从不曾与人群分离,
悲伤与怜悯把我们融为一体。
我常常说,我们已忘记自己是王的子民。
因为我们出生的地方,既不分
对和错,也无论现在,过去和未来
我们如此不幸,在漫长旅途中接受的
礼物,只用了很少一部分。
来自昨日与数百年前的众多时刻——
刀光鸣响,在擦亮的金属镜前
描画睫毛,步枪发出致命的射击声,一艘快帆
撞到暗礁,然后破碎——它们保留在我们心中,
期待着完成。
我早已知道,我将是葡萄园一名工人,
像同时代的所有男人女人那样,
无论他们是否察觉到这一点。
在这里,米沃什讲述了站在90岁门槛上看见的东西,包括诗的秘密和人生的秘密。我们的视野里,再没有比他年纪大还写诗的人了,他的见证,他的感悟,尤其珍贵。在少了是非对错、少了时间概念的地方,是一种悲悯之情,把他融在人群之中,不再分离。他的描述让人心有戚戚,他对生养之地的爱,与生俱来,在不得不远离时,越发浓重。
他这漫长的一生,虽然精通6种语言,虽然半个多世纪不在波兰,却一直用波兰语写诗。按他自传的说法,是欧洲的那个角落塑造了他,于是他用童年时所讲的母语写作,保持他的忠诚。
米沃什不喜欢人们解读他的诗歌,担心其中的误读。这样一来,我没有一句接一句解读他的诗,但仍想对他用母语写诗说点看法。如果我没记错,米沃什说过一件事,他使用的波兰语,在16世纪的几十年里,达到了文学语言上的成熟,此后没有大的改变。这让我吃惊,如果他说的成熟,与我说的成熟标准相似,那么在文学语言的成熟上,波兰语竟然早于世界上其他语种。
我找了几首米沃什诗歌的两种中译,一种译自波兰语原文,算是一手翻译;一种从英译本转译的,算是二手翻译。一手翻译与二手翻译比较,我没有见到多大差别,可见波兰语的文学表现力与英语同样出色,米沃什说它成熟是对的。
一个民族文学语言的成熟,怎么说都是件大事,而且与真正优秀的作家紧密相连。比如,英语的文学语言,到16世纪后期的莎士比亚开始成熟;俄语的文学语言成熟较晚,要到19世纪中期的屠格涅夫和契诃夫;日语的文学语言成熟更晚,甚至要到20世纪的村上春树。世界上也有一些民族,至今还没有成熟的文学语言,因此没有开阔、深入、生动、细腻的描述能力。根据这样的描述能力,你可以自行分析,古代汉语的文学语言、现代汉语的文学语言都是什么时候成熟的?
在接受诺贝尔奖的演说中,米沃什的一段话,说的是波兰文学的传承,也是文学语言的传承:“由于波兰文学的难译,使得它鲜为世人所知,而我却正是它的一分子。故与其他文学相比,我能体会其丰富的妙韵。这是一种与先人血脉相连而自成一格的神秘情谊,其中的哭泣与欢笑、悲怆与嘲讽,都是在同一步调下共存。”
这与一个人的文学创造力永远强大,有关系吗?
上面说的事情,其实是促使米沃什文学创造力持久和强大的几个因素:一是他要传承与先人血脉相连的母语;二是他觉得使用童年的母语时,对语言的把握是最出色的;三是他离开故乡故国,太远又太久,用乡音写他的乡愁,用母语保持他与故乡故国的精神联系;四是他相信只要写出很多很好的诗,他不得不离开的家园才会欢迎他归来;五是这个时间跨度太大,于是让他保持了超长久的、强有力的精神状态。
这样一来,真正让我们惊讶的,不是他写诗写到了90多岁,而是他90多岁的诗,仍然是质量极优的那一批。
特邀编辑:董学仁
满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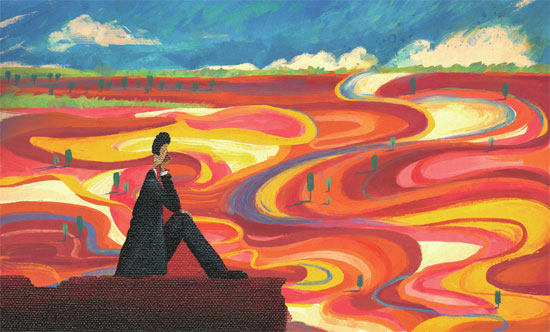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