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出生于中国造纸之乡——泽雅。泽雅,位于浙江温州瓯海区西部。境内有始建于唐龙纪元年的极乐寺,有明代的永宁桥,还有纸山文化——关乎古中国四大发明之一造纸术的做纸工艺。她是纸农的后代,自小熟悉并参与古法造纸术,青山绿水竹海水碓是她耳濡目染之物,是丰润的滋养,也成为她血液里弥灌的性情、灵感之源泉。
我说的是散文家、民俗研究者周吉敏。一个在山野自然中奔跑长大的女子,以草本植物涵养性情,以峰峦流水锤炼品格,温婉静姝的外表下暗藏坚毅、果决之气。
果然,在造纸与书写之间存有一条隐秘通道。许多年后,离开故乡纸山的周吉敏,回望来路,追溯往昔,打捞精神世界的碎片,陆续写下《民间绝色》《斜阳外》《古游录》等书。
《民间绝色》是周吉敏自觉写作的起始。在此之前,她写过大量的关于童年生活的小随笔——也是必不可少的语词训练和情感积累。2009年至2011年间,她尝试走出书斋去乡间行走,去采访年迈的手艺人,以文字和镜头记录泽雅古法造纸、彩石镶嵌、水上台阁、竹编、蓑衣等三十项濒临失传的民间技艺。采访过程中,一名编制竹丝灯笼的老人猝然离世,让她感到时间的窘迫与刻不容缓,更是加快了行走和记录的步伐,让更多的民间技艺被人看见。“写作让它们从技到艺,给予它们艺术的审美。”周吉敏如此说。
最终,《民间绝色》获浙江省民间文艺最高奖——“映山红”奖,这也是献给手艺人的赞歌。
一个写作者的内心诉求
由此肇始,周吉敏这一颗热爱民间文艺之心与故乡大地上顽固留存的东西相契、相遇,它们是还未被时间河流蒸发和带走的东西——荒草离离的古道、被谢灵运写入诗中的古塘河以及更多被遮蔽被遗忘的事物。还有温州籍散文家琦君,代表的是瓯越民俗,是乡愁、诗和远方,也是日常生活里最温润绵长的底子。她要以一己之力呵护、保存它们。
“一生爱好是天然”,这既是周吉敏为琦君百年纪念集所拟之书名,也是她自身性情品格之写照。自然、灵动、温婉、朴素,既可以用来形容一片绿叶、一束花卉,也是一个写作者的内心诉求,归于本性,遵从内心。
从民俗中研究历史,于人文地理中感受时光的深邃与浩瀚,周吉敏的文字里透着光,是行走及省思的产物,是今人与古人的碰撞,也暗含自身精神成长的印记。它温润、内敛、丰厚,有古玉的光泽,让人想起她家乡泽雅山上的古法造纸——从发酵到蒸煮,从捶打到水碓,最终成型的纸张其肌理饱满生动,其厚薄、韧性、光泽宛如艺术品,无可挑剔;文字的诞生过程也是如此,漫游,追溯,省思,观照,推倒,重塑……
最终凝练结晶而成,接受时间的惩罚或捶打,或化为尘烟遁走,或留下闪烁的光芒。
2012年至2015年,这四年时间内,周吉敏以双脚触碰、亲历瓯海境内的古道,并写下《斜阳外》这本古道之书。荒烟蔓草间,她辨认、丈量古人行走的踪迹,将自己的名字与温州大地上的十七条古道写在一起,它们是桐岭、小岭、分水岭、岷岗岭、船放岭、丽塘岭、外山岭、翠微岭、西山岭、吴坑岭、李山寨岭、林案岭、古耸岭、十二盘岭、天长岭、蜈蚣岭、卧龙路等。
作为人类过去时的存在,古道具有辨认历史、追溯过往的功能,既是地理空间的遗存,也是过去与未来的连接之路。如今,它空谷绝响,鲜为人知。
我想象一身布衣的周吉敏,走在春天野花遍地的深山里,走在秋天霜露微降、草木摇落的山岭上,以及冬日银白寒冷的荒野里。她也在雨中、雪后、山溪淙淙之时,接受山野古道的邀约,或携友同行,或兴冲冲独自前往。古道于她,就如故国家园,就如生命生息之源头。在那里,她获得精神的给养,风景、人事、古物、村落、街道、庙宇都是她热烈交谈的对象,关注它们的情绪、命运及在时间河床上的走向。她跌跌撞撞,心无旁骛,就像一个梦游人,一个过往时光的打捞者,幻想着与自己的童年、与祖先的幽灵邂逅。
为了找到那条最终的“路”
吉敏的古道之旅也是回溯之旅,但回溯从来不是为了回溯本身,而是为了找到那条最终的“路”,古人今人共同走过的痕迹,是文脉,是地理气韵,更是“一个村子集聚、迁徙、新人回归的过程”。
吉敏赠我一册《斜阳外》,扉页题词:古道尽头是故乡。我想起李叔同的《送别》,也想起童年走过的碎石路面,道畔野蛮生长的茅草及荆条几乎要覆盖和侵吞了它,但古道是不会消失的。行走是对古道最好的礼赞。尤其于心浮气躁的现代人而言,这一项类似修行的举止,那种喜悦、自足,彻底的无人状态,无可比拟。
整册《斜阳外》,最美好、最温暖的是关于行走途中草木自然的书写,那似乎是从吉敏的身体里流淌而出,无须多余修辞,早已触动人心。吉敏的文字让我体悟到什么是有温度的写作,客观之中有自我,冷静之余有体恤,让人产生强烈的融入感,成为那情景交融的一部分。情感永远是写作的触发器。没有情感,一切文字不过是纸上傀儡,大风一吹便烟消云散。
多年前,因为《斜阳外》这本书我知道了吉敏,以至脑海里总不断浮现出她在古道上踽踽独行的画面,总以修长的背影示人,总是那么温婉、热烈、清醒、坚定。究竟是作家赋予作品以生机,还是笔下的书写对象最终成全和塑造了写作者,这大概是双重的、互相“浇灌”的过程。
恰恰,吉敏最喜欢、最常用的一个词语是:情状。以情写景,以情状物,以情动人。情感是底座,是肌理,是万事万物的开端和发展。
到了《古游录》一书,在书斋和大地之间行走、往返的吉敏,更多了自由呼吸的空间。她以云的飘荡、水的奔泻、树枝的生长来写作和结构此书。她的世界更深阔、更庞大,也更为纷繁复杂了。她在南戏、傀儡戏、古寺残存的碑文中找到进入历史通道的“密钥”,里面光线昏暗、视物模糊,但她总有办法截取关键信息,以烛照时空真相。她知道既要从事物的表面,也要从事物的深处或厚度去描绘它,更要知其来历和去处。
吉敏笔下,历史成了可触、可感、可生发的对象,而不是故纸堆里干巴巴的碎片,毫无生命迹象的史料。好像,她有一种抟捏揉搓的本领,或者说她手中握有一件他人孜孜以求的“法器”,足可串联起历史深处的幽微及磅礴,细腻与芜杂,将不可辨认之物准确、清晰地呈现出来,也将不可描述之时空人事累积成一个可能的艺术的样式,以婉转、以细致、以机敏,更以无限的热诚和耐心。
所有文字都是热情的产物。这个“情”是专情、是深情,唯其“专”和“深”才能抵达事物及人性之内部,之本质。同样,好文字能拨开浮世的尘烟和迷障,让人心安然、妥帖、自在。
以一己深情来“化用”文献史料
历史文化类散文的书写,最忌以论带史和堆砌史料。对此,吉敏有自己的思考和写作践行。在我看来,无非是一个字:情。与其他写作者惯用知识记忆来堆垛史料不同,吉敏以情感,甚至以一己深情来“化用”文献史料,来暗示感受与体验,从而表现某种共通的心境。不得不说,“情”是催化剂。对历史人物心境、情绪的体察,对当时当地生活细节的观察和想象,让她在文献及史料的迷宫里自如往返,总能不枝不蔓,从容抓取核心。
她总能将历史尘烟中散乱的时空地图连缀起来,以一种貌似即兴的、漫不经心的方式,将细节、天气、景物以及细微感受嵌入其中,形成一种“漫游”式的书写风格。而落脚点永远在现在、在今天和在此刻。
《隐蔽的李唐血脉》一文中,那个一心想要恢复先祖故宅的李成木老人,奔走十余年,仍一无所获。通过李氏子孙对祖先李集的回忆和寻找,想象和重塑,我们似乎看到写作者的终极意图,即个体如何在血脉迁徙及时间流逝中,认清自我,辨认自我,找到自我。
吉敏的转换不仅发生在文献资料和当下生活之间,也在观照他人和自我观照之间,文本内部的空间因此深阔、复杂和奇异。它是语言、地理及历史空间的多重组合及交织。既是语言的编织,也是思想的融合,后者不是艰深学理和哲学思辨,而是一个普通写作者于史料基础之上对古人、对过往生活的一种体认和追忆,或许还有想象和重构。
《古游录》中,文字的华彩更是俯拾即是。任何文本,文字的肌理就如织物的纹理,给人最直接、最本质的审美冲击。字词的质感、语句的韧性以及彼此之间的呼应及融合,是为肌理。吉敏天生懂得如何呈现它,文字调性为娓娓道来,节奏则疏密有致、长短交杂,既短促有力又绵密幽邃,既有氤氲,也有锤炼。朴素中暗含惊艳。平常叙述中,常有异质的东西来互补和对冲,形成一种摇晃、跳跃,蜿蜒升腾之美感。读者总能于寻常表达中读出惊异和陌生感。
历史的幽微与深邃,或许比它的博大和广袤更吸引人,更能成为文学生发的土壤。《古游录》的文学性正体现在它对微小感受的放大,以及历史中日常场景的想象和呈现上。人在特定环境中的体悟、感受、反应通过一个细节、一幕场景,直观而感性地展示。字字落到实处,但猛然回首,整个地又忽然虚化起来,宛如高空俯瞰,宛如隧道外张望,时间赋予一切以距离感和纵深感。
《古游录》呈现出历史文化散文写作的另一种可能性,温煦、淡然,意在言外,又生机勃勃。它将沉甸甸、化不开的典籍史料分解、融化在叙述推进中,并搜寻精神线索以激活它,增加细节和个人感受,注重展示历史和个人的关系,以及人如何在其中找到归属。它是写作者的精神历险,也是灵魂之旅。
古人、古物、古习俗和古文艺不过是载体,是写作生发和书写的对象,而精神领域内的碰撞、燃烧、回归,才是根本。以行走建立坐标的吉敏已然找到属于自己的写作方向,以双脚行于大地之上,何尝不是行走在时间和历史深处。她以独特的方式感受、聆听来自远古的声音,那声音必将指引着她去寻找精神领域内的冒险与共鸣。
从《民间绝色》《斜阳外》到《古游录》,三册书籍呈现出吉敏对逝去之物的深切回望。从传统技艺至古道,至浩渺的历史时空,她的书写变得愈加开阔而自由。吉敏的来路清晰而一以贯之,由童年山水获得的滋养,慢慢转化为她对故乡大地的深情,于是,所有写作便成了收集美与光亮的旅程。
特邀编辑:只恒文
草白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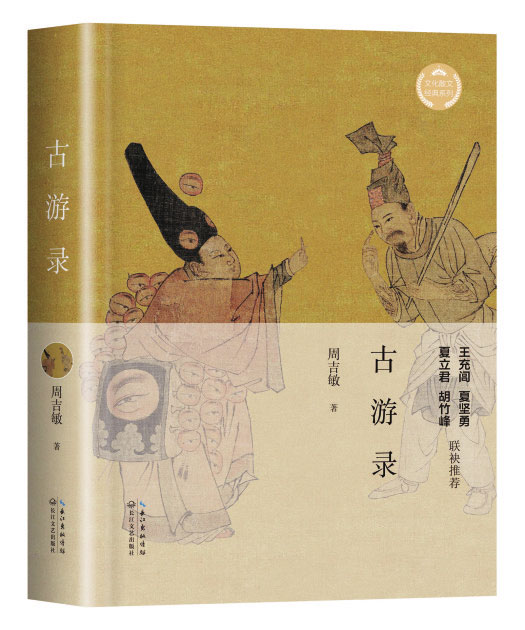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