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
“他家希望你们到来,我先把相关资料发给你们,到时候到了给我打电话就行。”苦苦等待三天之后,大坝村张主任打电话过来,实在给我们一个莫大的惊喜,这也就意味着,我们的志愿服务之路即将开始。
他叫阿贵,准高三毕业学生,除了他,家中另有相差七岁的阿弟,在镇上小学念五年级。阿贵爸常年在外务工,家中所有重担全由阿贵妈肩负。浏览着他们家的背景信息,不由得一震,我心里描绘起他们的容貌来。
我向来相信缘分,冥冥中能与他们相遇,实则也算幸运。
心中的怡然并未刻意外露,而是想着该给他们备些什么。看着学校图书馆楼顶旁的斜阳,我脸上不觉泛起红晕,那是一位怯弱少年再一次踏上救赎之路的喜悦。
足迹
由重庆至涪陵,我们并未乘坐高铁,而是选择了高速客车,这样可以欣赏沿途的乡村景象。
掀开窗帘,清晨暖阳照进车内,城市的高楼逐渐远去,农村的矮小楼房不断涌现。曾经瓦砾土楼的房屋,大多变作二层精致小洋房,显得生机盎然,充满朝气。
到达涪陵后,我们购买了去往青羊镇的客车票。候车室内,邻座的孩童显然耐不住等候,不顾他母亲训斥在座位上闹腾。汽车枢纽站不久前竣工,与老车站相比,多了几许派头。事物不断向前发展,对这里的居民而言,可说是不错的兆头。
去往镇上的客车行驶在较为狭窄的国道上,这已有多年历史的道路见证了沿途村镇的兴起与发展,如今也快到了退休的时段。不久之后,一条宽阔笔直的四车道将接替它的任务。
“这边!总算等到你们了。”张主任在街的另一角招手示意我们过去。他的嗓门打破了镇子的寂静,我们受宠若惊。
“今天,街上没多少人走动。”他逐一与我们握手,热情洋溢在他的脸上。额头的皱纹与手上的老茧,不仅暴露了他的年岁,也彰显了他的厚道与朴实,这是农民惯有的形象。
天色已晚,去往阿贵家还需走上许久的山路,只得明日再动身前往。
趁夕阳还未落幕,我们环顾村子四周,几户瓦房显得格外刺眼,多是十多年前旧式二楼平房。还好,正值夏季,若是到了冬秋季,整个村子足能给人以破败与沧桑之感。
这一番景象,让我想到了梁鸿老师曾在《中国在梁庄》中写道:“从什么时候起,乡村成了民族的累赘,成了改革、发展与现代追求的负面?什么时候起,乡村成为底层、边缘、病症的代名词?”虽说写于十几年前,但在这里,依旧看到了那时梁老师笔下梁庄的影子。
明日见着阿贵,该是以怎样的方式开始?又该如何继续?一切都是未知,不由得我在即将睡去时遐想。
那山,那屋,那少年
“阿贵妈,我们来了,出来接接我们。”张主任在狗吠声中带着我们向阿贵家走去。好在阿贵妈赶忙出来呵斥她家的黑狗,不然随同的我们不敢轻易靠近。
阿贵妈是典型的农村妇女,四十岁左右,微胖,其实是壮。这也难怪,辛勤打理家庭上下使她早已褪去属于女人的娇柔。
“阿贵、阿弟,快出来欢迎哥哥姐姐。”热情招呼我们之后,她在拿出凳子的同时呼唤楼上的阿贵与阿弟。我们坐在屋子门前的坝子外,椅子什么样式都有,农村四方小凳、高长凳与低四角凳,能看出阿贵妈有意为我们准备了三个崭新小方凳,于是打趣说道:“阿姨,还好我们人不多,不然让你买凳子都破费不少吧?”说完笑起来。
阿贵走了出来,兜里揣了什么,正挨个分给我们。“知道你们来,他跟阿弟前几天一同在镇上买了软糖。”仍是阿贵妈笑着对我们说。糖分完后,阿贵嘴边带着腼腆的笑容坐在了他母亲旁。
在打量阿贵的同时,阿弟也走了出来。他的步态有些僵硬,像是做了错事心虚似的,逃避视线不让我们察觉。
“阿贵、阿弟,你们在家里做什么呀?”为了增进与他们兄弟间的距离,我们将话题转移至他们处。
“他做暑假作业,我在线上做家教,挣些钱用于生活。”说话的是阿贵,眼神有些呆滞,在低头看向地面的同时也不时用余光扫过眼前的我们。一旦眼神与我们对视,随即低头沉默。阿弟始终不语,即使被提及也只是简短回应。
“这俩孩子,平时在家很会唠嗑,今天却当哑巴了。你们别介意,人多他们话就不多。”阿贵妈略微带着歉意向我们解释,我们只得不再为难他俩,将话题又转移至别处。恰好阿贵奶奶在距离几十米远向我们招手,见她背篼里装着什么东西,我们一齐前去搀扶,话题自然也就转移。
后来我想到,阿贵和阿弟的沉默,并非是不善言辞,而大致是出于农村孩子在我们面前的无措,但也只能说是大致而已。
午后,我们为阿贵家准备的礼品送到了他们家里。除了牛奶、麦片等老少皆宜的补品外,特意为阿弟准备了新的书包与衣裳,还有给阿贵精心挑选的被褥。知道他俩需要上学,尤其是阿贵,大学对他而言将是另一个世界。
夜幕降临,我们借着月光走在回去的路上。与阿贵一家短暂告别之后,我们也即将做进一步服务计划。
不过,回过头望向那片山时,阿贵家如同云海里的星宿,发出微弱且孤独的光。
我想,他们一定也有过向往,若最初的起点不是在这群山里,那这两个少年命运轨迹是否也会改变?我沉默,答案是肯定的,但想到有些事发生了就已成了事实,这样的幻想还是不需要念着才好,更别让他们知道。
“我想撑起这家”
“阿贵妈?这边两户人家去哪里了呀?”我们帮阿贵家晾晒青菜头时,偶然看见了另外两户房屋,但都已破烂不堪,只是我们昨日没有发觉。
“他们都搬去城里了,山里可留不住他们。”她没有停下手中切菜头的活儿,笑着答复我们。她知晓我们说的是哪两户人家,从她的语气里,听不出对搬进城里的两户人家是羡慕还是不以为然,但能肯定的是,她享受此时的生活。
傍晚,我与另一位志愿者决定留在阿贵家里,倒不是被白天农活给累的,而是想进一步了解阿贵与阿弟。他俩白天也没少受累,不仅与我们一同收菜头、割羊草、捆玉米、挖红薯,还得兼顾作业与家教。白天里的那些农活儿他们已经做了好些日子,甚至说好几年光阴也不为过。那是每一个山里孩子的拿手绝活儿。
“小阳,你们知道手机上怎么看视频不?还有,我听说手机有什么微信,里面可以抢红包,还有什么朋友圈,可以跟别人聊天啥的……”
听完阿贵妈这番话,我和另一位志愿者心里有点哽咽。这是我们熟知的娱乐时代,但那些似乎被时代遗忘的人,心里积的雪我们从不曾看见。
(未完待续)
特邀编辑:董学仁
责任编辑:宋宝颖
湖南师范大学硕士生 汪阳(22岁)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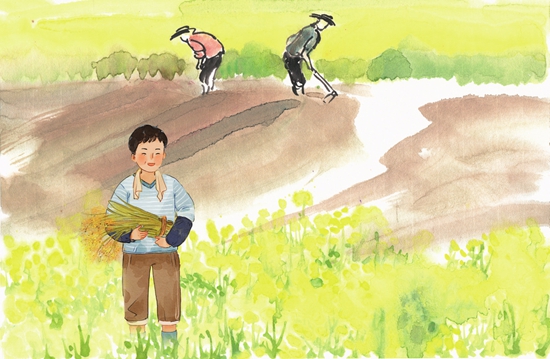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