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作家韩静慧长篇小说《锔盆女孩》改编的同名音乐剧在北京物资学院运河大剧场亮相。音乐剧优美的歌舞和唱词,把观众带到了700多年前的大运河畔,来自草原的女孩赵吉儿面对苦难时的顽强善良和坚韧,古代运河边老匠人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让现场的观众无不动容。
“《锔盆女孩》这部音乐剧改编自同名小说,小说与大运河文化遗产修缮保护利用的出发点不谋而合。读者在优美的故事中既学习了历史、又了解了大运河的文脉。这本书和这部音乐剧就像一把金钥匙,打开了元代大运河历史风貌的大门。”大运河文史专家任德永说。
韩静慧也在现场观看音乐剧的首演。在小说中,赵吉儿是元代大德年间的一个普通少女,和母亲女扮男装来大都寻找父亲。为了活下去,母女二人去船上打工。在搬运瓷器的过程中,母亲失手打碎了贵重瓷器。赵吉儿在兜着瓷器寻找锔匠师傅的过程中,下定决心去学习这门手艺。最后也正是因为学到了这种手艺,才为自己赢得了尊严。
韩静慧说,为了写好这本书,她深入了解了元代大德年间的政治制度、人文环境,以及当时的风土人情、民俗文化,老通州城街道布局等细节。因为小说中赵吉儿母女进入大都后的第一站就是积水潭,木匠赵庆是元大德年间到元大都修水闸的,但至于赵庆在哪个闸工作,母女俩并不知道,于是一路寻亲到通州的漕运码头。
为了准确地搞清楚二十四闸到底在什么地方,韩静慧从通州码头出发,一路寻找。“我是个认真的人,既然想写就要尽量贴近历史,尤其是地名。虽然是文学作品,但因为涉及到运河,地名最好准确一点。”韩静慧说。
2024年7月韩静慧在电台做节目时,主持人问她:“大运河是如何成为你小说故事背景的?”韩静慧回答说:“运河是水上的瓷器之路,运河边的人民依靠运河而生活,其中一部分是依靠卖瓷器、运输瓷器、搬运瓷器而生存的,随着瓷器的兴盛自然就演变出一种职业:锔瓷匠人。另外我就生活在大运河边,常常沿着玉带河(玉带河西街)到运河边转悠和锻炼,有一天在夜深人静马路上没有行人的时候,我竟然神经质一样将耳朵贴在地面上,想倾听地下流水的声音。因为这条路在1986年之前还是通州城的护城河,后来城市改造才变成了路。虽然我听不见马路下面的水流声音,但我满脑子浮现的都是这条河围绕着通州城慢慢流动的优美身姿。”
韩静慧说,彼时她仿佛变成700年前的古人,“融入在运河边各种装束的人群之中,和他们一起看百船聚集,千帆竞泊的古代运河盛景;听纤夫拉船时那种生命的呼喊和铁锚的撞击声;听岸边歌台酒肆传出来的民间歌曲;再走到西海子看燃灯塔,和塔上的风铃对话……大运河两岸的所有一切都自然流泻出来,所以大运河无法不成为《锔盆女孩》的故事背景”。
《锔盆女孩》的第14章和第15章把锔匠老师傅向赵吉儿传授绝活的过程写得活灵活现。老师傅对赵吉儿的教育处处蕴含着人生的哲理,而丁娃子和吉儿之间关系的描写则处处彰显人性。“老师傅为什么没有把技术传给跟他学艺时间最长的大徒弟丁娃子?不但不教,还嘱咐吉儿学会了也不要教给丁娃子。师傅告诉吉儿:丁娃子是个心气不稳的孩子,脾气个性都不适合,他学了这门手艺不会有好处还会毁了自己。这门手艺在开始准备阶段就考验着一个人的定力和智慧,黄豆和水的量是根据壶的大小来定的,放多了会把壶撑碎,撑得太碎的壶就无法复原,就成了废品,还得赔顾客几倍甚至几十倍的价钱。”韩静慧说,那时的锔瓷不仅仅是养家糊口的手艺,也是缝补心灵缺憾,修复生命的唯美艺术,在小说《锔盆女孩》里,“它更是修复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关系的重要文化符号”。
韩静慧家里曾有4个古代的彩绘茶瓶,其中两个都有裂纹,但裂纹的两端都被褐色的铜钉钉在一起。“像挂在裂纹两边一片片精致的小树叶,倒给茶瓶平添了几分姿色。”韩静慧说,儿时家门口走街串巷挑着担子摇着铃铛“锔盆锔碗锔大缸吆”的老锔匠,不仅跃进她的脑海,也跳到小说《锔盆女孩》的字里行间,像是五线谱上活泼灵动的音符,编织成一首优美的乐曲。
无论是《额吉和罂粟花》中善良隐忍、甘于自我牺牲的额吉,《摇摆不定》里那个坚强勇敢、冲破世俗眼光的知识分子诺敏,还是《锔盆女孩》中执着顽强、用手艺活儿赢得尊重的赵吉儿,韩静慧小说中的女主人公都有着自尊自爱、独立自强的性格,这和韩静慧自身的成长经历是无法分开的。她笔下的女性人物更像是她不同成长时期的缩影,而她也想通过故事让更多的女性成长为坚强果敢、勇于担当、独立自强的人。
夏日傍晚,微风吹拂,掠动平静的大运河水面,泛起层层涟漪。从东岸向西眺望,瑰丽的晚霞映入眼帘,朵朵红云在天光中变换形状,如梦似幻。燃灯塔像婀娜的女子,矗立在大运河畔,见证着因水而兴的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发展。而大运河的通达天下,燃灯塔的声声铜铃,正一点点浓缩在韩静慧的一部部作品里。
责任编辑:周伟
翟祚珩 本报见习记者 赵小萱 记者 周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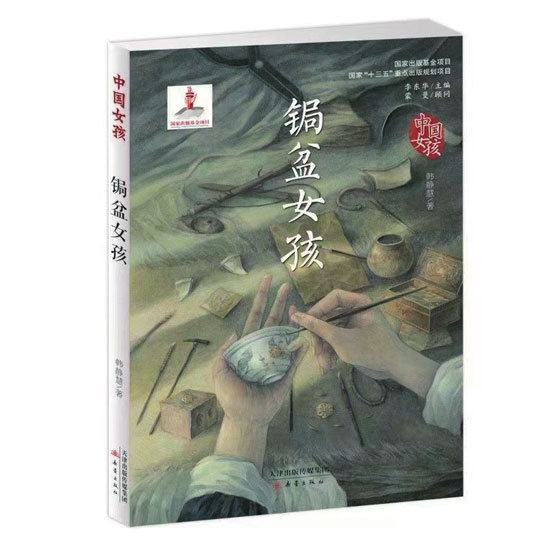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