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去上学,第一站永远是从镇上出发到城里的“农班车”。
准确地说,路程的开始,是弯弯绕绕、一下子看不到头的乡间小道。十几年前的月亮又大又亮,把路照得很敞亮,奶奶总说,现在新装的这些路灯,远不如那时的月亮要亮。地面上树影婆娑,来时像在欢迎我,离别瞬间却又似乎在挽留我。伴着凌晨时分潮湿的空气和星星点点的泥土味,我出发了。
在这条路上一直陪伴着我的,是奶奶的叮咛。从小学起,奶奶就会陪着我走过这条路,因为当时这条泥巴路是村子通向外面唯一的一条道。晴天还好,若是碰到下雨,奶奶便背着我,把裤脚卷到大腿,一步一步从满是泥泞的小道里走出来。奶奶心疼我,可我也心疼她,不论我多少次想要下来,那双托着我的手只会更紧一分。
“好啦好啦,你要下来走,鞋子弄脏了怎么去学堂呀?要好好念书,知道啦?”
我更加扣紧了奶奶的肩膀,暗暗在心里下定决心,一定要努力读书。
后来村里条件好了,在这条早已不成样子的路上铺上了碎石,走起来方便多了。我也考上了城里的中学,因为住校,回家的次数少了很多。但每次回来都还是像以前一样,从踏上返校路的开始,奶奶的嘱咐就没断过。小到我的起居,大到我的学业人生,总不会落下任何一个小点。奶奶是驼背,听说是她小时候挑担子压的,年轻时还不觉得,可越到后来,她的背就越驼。从前的我总是会摸着她那凸出来的脊骨,一遍遍地问她疼不疼。奶奶那布满细纹深深凹陷下去的眼眶里,能流露出许多情绪来。我看见的,是对往昔的回忆,是对我贴心地欣慰,是对熬过那段时光的感慨,是对现在美好年代的感恩。待这些复杂的情感融合到一起,她会转过头来拍拍我的头。
“不疼,就是走路累点,我的乖孙。”
中学住校的日子里,每隔10天,那样上下学的路才会循环一次。奶奶总是会抢过我的书包去背,她说她直不起腰,走路累,非得背点什么在背后,才能把弯着的腰背直点,这样走起路来才更松快些。
可是她错了。这样的话,掩盖不了她的气喘吁吁,隐藏不了她越来越慢的步伐,更是骗不了我。于是我开始偷偷掉包,把那些重的东西全部塞在我衣服的包裹里,将那些轻巧的、占地方的东西放到书包里,如此便使我愧疚的心灵得到一点点救赎。
后来,村里建了厂子,每天都有数不清的货物往外运,就修了条柏油大路,来往的车辆就在这条路上不停地往返,后来又修了条水泥路,专门给村民出行。就这样,这条小路演化成了现在的形态。
要说最开心的,莫过于奶奶,她走了一辈子的破路烂桥,她的子孙终于不用走了。
“以后就好了,你回家我就在马路口等你,让你爸给你买个和城里小孩一样的拖拉箱,少受点罪。”
奶奶年纪大了,在我中学的最后一年,她的背彻底弯下去了,再直不起来。可在这条路上,她却还要为我做些什么,坚持要帮我拎个包袱。因为高三,10天的轮回周期变成了一个月,即便这样,我也不忍心让奶奶替我拿东西,甚至这段路,都不想让她多走。但奶奶也是犟的,硬是在我走出百米后从家里出来跟上我,夺过我手里的袋子。我知道奶奶是甩不掉的,她会一直在我身后,陪着我。结果就是,我又将袋子里的东西减轻重量,把那些沉的东西全部都压缩在行李箱里。
小路的尽头,是镇子到城里的马路,路口有公交站,可以坐上去火车站的“农班车”。
上车的站口在马路对面,奶奶总不放心我。不论我已经长到多大的个子,她还是会走在我前面,等两边都没车之后,急促地叫着我一起快速通过。高三那年,她便再没和我一起过去了,只是在马路对面看着我,看我上车后,才会转身回家。
踏上“农班车”的那一刻,这条小路就算是真的走到了终点。来不及收拾行李,通常我会直奔靠窗的座位,因为那样能看见奶奶回去的背影。
可是每一次,那个瘦瘦小小的身形都和我记忆里的有些许偏差。什么时候她的腰弯成了那样?几乎呈90度。又是什么时候,奶奶的头发日渐褪色,走在这条新路上,显得格格不入。
奶奶在这条路上,陪伴了我许多年,而她与这条路的命运却好似相反。
开始和终点,这条路的距离,原来那么短。
见习编辑:郑欣宜
责任编辑:周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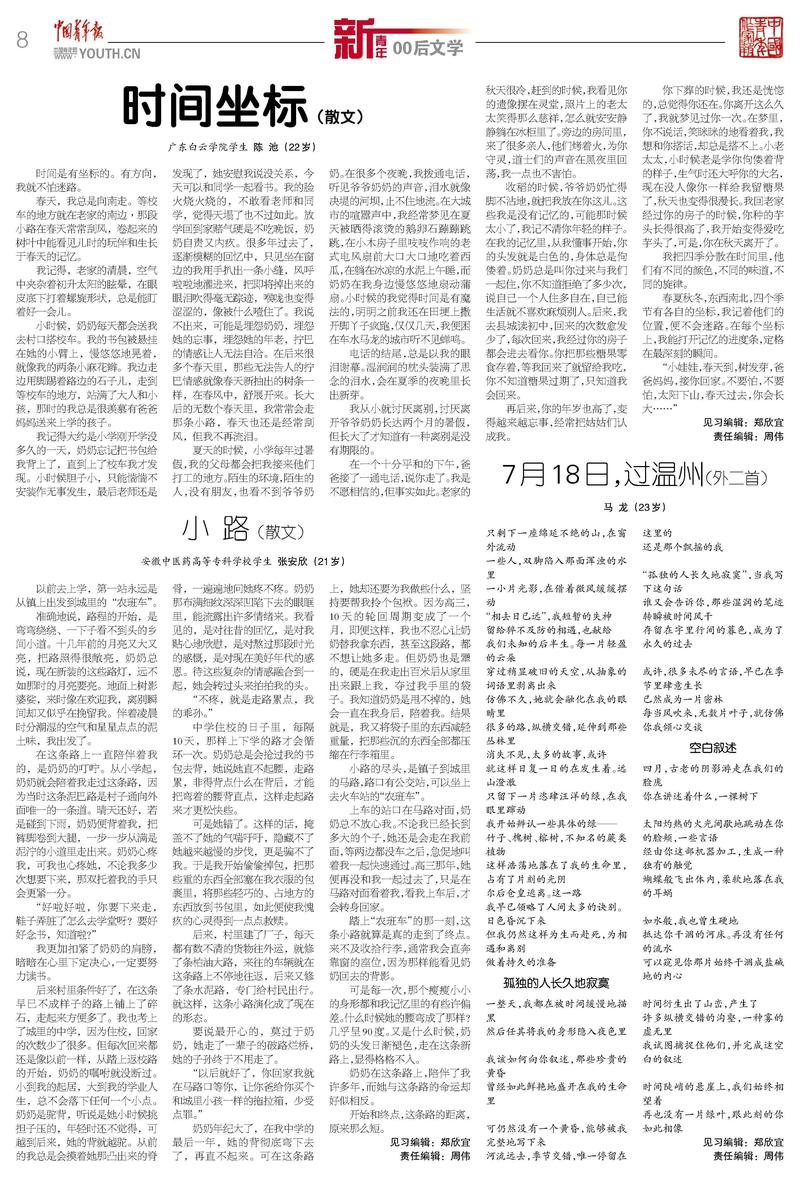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放大
放大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