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霞渡海时(小说)
山东政法学院学生 宋雨萱(18岁)
来源:中国青年作家报
(2025年04月15日 01版)

太阳尚未突破海平面,漆黑的天空中点缀着点点晓星,倒时差的痛苦使我于异国的车厢中惊醒。五颜六色头发的人歪七扭八睡着,只有李和坐在行李箱上精神饱满、容光焕发,他轻轻地用袖子擦拭他视若珍宝的枣木盒,盒角磨损的铜包边在顶灯下泛着幽光。
“姑娘快瞧,云母片都备齐了。”他掀开盒盖,30年前的老报纸里裹着各色矿石。“当年给龙王爷塑金身,须得用辰州砂调出正红,拿青州石磨出翠色。这云母碾成细粉掺进釉料,烧出来的龙鳞能在日头底下泛彩呢!”李和抚过矿物标本,浑浊的左眼突然泛起异样神采,仿佛穿越时空望见了永乐年间香火鼎盛的东岳庙。
我的思绪早已飞到九霄云外,只下意识应和着。李和也不在意我的敷衍,仍旧轻飘飘地坐在行李箱上唠叨,口若悬河、酣畅淋漓,偶尔话题还会回到我身上。
“你莫要老盯着那典籍看了,时间久了,眼睛会像我一样的。”
“是记者的工作计划,不是典籍啦,我就回顾一遍。”我翻着红绒面手册,漫不经心地纠正道。这趟旅行本是杂志社里派我远赴异国拍摄一些新版块所需的材料,不过是看李和可怜、又顺路才带上了他,所以一路上我更专注于自己未完成的工作,放任他在一旁滔滔不绝。不过这副话痨的样子,实在是和3个月前我在晋南村志编纂处初遇他的时候——当时李和正用放大镜逐字校对手抄本《琉璃志》——闷头苦干、羞涩木讷的情形大相径庭了。
当第一缕晨光刺破泰晤士河的薄雾时,李和突然挺直佝偻的背脊。隔着氤氲的咖啡香气,我看见他平和敦厚的面庞被镀上金边,修长的右手悬在半空描摹着想象中的飞檐斗拱:“当年在曲沃城烧制琉璃塔刹,开窑那日也是这般霞光。36个时辰的窑火,2400片龙鳞瓦,青釉里融着辰砂……”
我安顿好行李,随手把册子夹在腋下,匆匆赶往第一个目的地。李和也极不情愿地跳下来,踉跄着抓住我的臂弯,布鞋在光可鉴人的大理石地面打滑。虽然他还是会对着路边喷水的石膏雕塑瞠目结舌、呆愣半晌,不过好歹有些长进,不再把汽车鸣笛声当作晴天里响了个霹雳了。
“到了!”李和顺着我指的方向望见了入口,立刻欢欣地向前冲去。等到他兀自跑进大门,消失在这栋名为“British Museum”的建筑的茫茫人海里时,我才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可还来不及思考,答案就已经展现在眼前了。
我很快就找到了李和。在33号展厅幽暗的射灯下,时间仿佛突然凝固。李和保持着俯身端详的姿势,后颈凸起的骨节在皮肤下颤动。展柜里,20块龙纹残片像被肢解的龙尸陈列在丝绒衬布上,断裂处新补的石膏白得刺眼。他用颤抖的指尖隔着玻璃描摹龙角残缺的纹路,突然发出受伤野兽般的呜咽:“这龙睛本该镶着鸽血红……你们说的保护,就是拿洋灰糊我的龙鳞?”
他轻轻地呢喃着,目光却好似审讯室的两束白炽灯光狠狠刺痛了我的眼睛。
我的快门键迟迟按不下去。取景框里,李和那掺着几丝白发的发梢与展签上“15世纪中国建筑构件”的英文说明重叠,电子讲解器里正用标准牛津腔讲述着“东方帝国的艺术馈赠”。斜对角展柜的希腊浮雕完整如新,保安手持禁止触摸的警示牌来回逡巡,却放任几个嬉笑的学生将热饮放在商周青铜鼎的展台上。
“妈妈快看!这条龙在哭呢。”稚嫩的童声刺破压抑的沉默。穿熊猫卫衣的男孩踮脚指着残损的龙须,“它是不是想游回水里?”年轻的母亲慌乱地瞥了眼英文说明牌,用上海话轻声纠正:“不要瞎讲哦,这是明朝的龙纹琉璃瓦……”伴着她的吴侬软语,李和正用裱画师修复古卷的姿势,将脸贴在展柜玻璃上,泪滴蜿蜒而下。
红绒面册子落地时惊起细微尘埃。我突然有种不太好的预感,伸手去抓李和,他却被惊得打了个哆嗦,佝偻的身影在晨光中渐渐透明……
“姑娘知道吗?晋南有座无梁殿,每逢谷雨,朝阳会从第九片龙鳞瓦开始,把整个屋脊染成金红色……美得像做梦。我就想把这梦变为现实,可这身体还是没等到最后。谢谢你成全了我的梦。不过我想,我该走了。”李和自顾自地嘟囔着,神情满是疼惜,恋恋不舍地盯着琉璃瓦,“可惜不能和它们一起啊。姑娘,等它们能见太阳了,能回家了,麻烦你千万告知我一声呀!”
他的声音随着身形消散在空调出风口的嗡鸣中,唯有展柜里的残片在恒温恒湿的囚牢里继续着第六个世纪的沉默。
我蹲下身捡拾散落的笔记,泛黄的宣纸间飘落半片龙鳞瓦拓印——这是李和生前最后的作品。1948年的县志记载,他在失明前夜仍执着地修改釉料配方,直到蜡烛燃尽了最后一滴泪珠时,留下了字迹歪歪扭扭的一生执念:见一次成品龙纹琉璃。
精确到“三钱六分孔雀石,二两八钱玉田砂”、融进了蜡烛和李和的眼泪的配方,此刻正尘封在大英博物馆的地下库房,编号1936,0728.56。拍立得缓缓吐出的照片被夹进记录宝贵见闻的红绒面册子里,我把它捂在心口,而后静静地看着那些展品,仿佛在看一条曾经波光粼粼、如今却停滞凝固的、历史的河流。
我突然想起楼兰壁画上剥落的朱砂,想起顾恺之《女史箴图》上东瀛收藏家的钤印,想起天龙山佛像脖颈处整齐的切割痕。玻璃展柜里的温度计恒定在20℃,却冻住了所有关于故土的记忆。当那个小男孩指着龟裂的漆器问“它们会想家吗”,我忽然听见万千文物的呜咽在穹顶下共鸣。
它们漂泊四海,应该比此刻的我更想回家吧。
暮色中的特拉法加广场华灯初上,我抱着红绒面册子坐在石阶上。霓虹灯牌在纳尔逊纪念柱上投下变幻的光影,恍惚间,那些光斑竟拼凑出李和临终前描绘的场景——某个霞光万里的清晨,修复完成的龙纹瓦当将被重新安置在故乡的庙宇之巅,釉色里的云母仍在等待真正的朝阳。
见习编辑:郑欣宜
责任编辑:周伟

太阳尚未突破海平面,漆黑的天空中点缀着点点晓星,倒时差的痛苦使我于异国的车厢中惊醒。五颜六色头发的人歪七扭八睡着,只有李和坐在行李箱上精神饱满、容光焕发,他轻轻地用袖子擦拭他视若珍宝的枣木盒,盒角磨损的铜包边在顶灯下泛着幽光。
“姑娘快瞧,云母片都备齐了。”他掀开盒盖,30年前的老报纸里裹着各色矿石。“当年给龙王爷塑金身,须得用辰州砂调出正红,拿青州石磨出翠色。这云母碾成细粉掺进釉料,烧出来的龙鳞能在日头底下泛彩呢!”李和抚过矿物标本,浑浊的左眼突然泛起异样神采,仿佛穿越时空望见了永乐年间香火鼎盛的东岳庙。
我的思绪早已飞到九霄云外,只下意识应和着。李和也不在意我的敷衍,仍旧轻飘飘地坐在行李箱上唠叨,口若悬河、酣畅淋漓,偶尔话题还会回到我身上。
“你莫要老盯着那典籍看了,时间久了,眼睛会像我一样的。”
“是记者的工作计划,不是典籍啦,我就回顾一遍。”我翻着红绒面手册,漫不经心地纠正道。这趟旅行本是杂志社里派我远赴异国拍摄一些新版块所需的材料,不过是看李和可怜、又顺路才带上了他,所以一路上我更专注于自己未完成的工作,放任他在一旁滔滔不绝。不过这副话痨的样子,实在是和3个月前我在晋南村志编纂处初遇他的时候——当时李和正用放大镜逐字校对手抄本《琉璃志》——闷头苦干、羞涩木讷的情形大相径庭了。
当第一缕晨光刺破泰晤士河的薄雾时,李和突然挺直佝偻的背脊。隔着氤氲的咖啡香气,我看见他平和敦厚的面庞被镀上金边,修长的右手悬在半空描摹着想象中的飞檐斗拱:“当年在曲沃城烧制琉璃塔刹,开窑那日也是这般霞光。36个时辰的窑火,2400片龙鳞瓦,青釉里融着辰砂……”
我安顿好行李,随手把册子夹在腋下,匆匆赶往第一个目的地。李和也极不情愿地跳下来,踉跄着抓住我的臂弯,布鞋在光可鉴人的大理石地面打滑。虽然他还是会对着路边喷水的石膏雕塑瞠目结舌、呆愣半晌,不过好歹有些长进,不再把汽车鸣笛声当作晴天里响了个霹雳了。
“到了!”李和顺着我指的方向望见了入口,立刻欢欣地向前冲去。等到他兀自跑进大门,消失在这栋名为“British Museum”的建筑的茫茫人海里时,我才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可还来不及思考,答案就已经展现在眼前了。
我很快就找到了李和。在33号展厅幽暗的射灯下,时间仿佛突然凝固。李和保持着俯身端详的姿势,后颈凸起的骨节在皮肤下颤动。展柜里,20块龙纹残片像被肢解的龙尸陈列在丝绒衬布上,断裂处新补的石膏白得刺眼。他用颤抖的指尖隔着玻璃描摹龙角残缺的纹路,突然发出受伤野兽般的呜咽:“这龙睛本该镶着鸽血红……你们说的保护,就是拿洋灰糊我的龙鳞?”
他轻轻地呢喃着,目光却好似审讯室的两束白炽灯光狠狠刺痛了我的眼睛。
我的快门键迟迟按不下去。取景框里,李和那掺着几丝白发的发梢与展签上“15世纪中国建筑构件”的英文说明重叠,电子讲解器里正用标准牛津腔讲述着“东方帝国的艺术馈赠”。斜对角展柜的希腊浮雕完整如新,保安手持禁止触摸的警示牌来回逡巡,却放任几个嬉笑的学生将热饮放在商周青铜鼎的展台上。
“妈妈快看!这条龙在哭呢。”稚嫩的童声刺破压抑的沉默。穿熊猫卫衣的男孩踮脚指着残损的龙须,“它是不是想游回水里?”年轻的母亲慌乱地瞥了眼英文说明牌,用上海话轻声纠正:“不要瞎讲哦,这是明朝的龙纹琉璃瓦……”伴着她的吴侬软语,李和正用裱画师修复古卷的姿势,将脸贴在展柜玻璃上,泪滴蜿蜒而下。
红绒面册子落地时惊起细微尘埃。我突然有种不太好的预感,伸手去抓李和,他却被惊得打了个哆嗦,佝偻的身影在晨光中渐渐透明……
“姑娘知道吗?晋南有座无梁殿,每逢谷雨,朝阳会从第九片龙鳞瓦开始,把整个屋脊染成金红色……美得像做梦。我就想把这梦变为现实,可这身体还是没等到最后。谢谢你成全了我的梦。不过我想,我该走了。”李和自顾自地嘟囔着,神情满是疼惜,恋恋不舍地盯着琉璃瓦,“可惜不能和它们一起啊。姑娘,等它们能见太阳了,能回家了,麻烦你千万告知我一声呀!”
他的声音随着身形消散在空调出风口的嗡鸣中,唯有展柜里的残片在恒温恒湿的囚牢里继续着第六个世纪的沉默。
我蹲下身捡拾散落的笔记,泛黄的宣纸间飘落半片龙鳞瓦拓印——这是李和生前最后的作品。1948年的县志记载,他在失明前夜仍执着地修改釉料配方,直到蜡烛燃尽了最后一滴泪珠时,留下了字迹歪歪扭扭的一生执念:见一次成品龙纹琉璃。
精确到“三钱六分孔雀石,二两八钱玉田砂”、融进了蜡烛和李和的眼泪的配方,此刻正尘封在大英博物馆的地下库房,编号1936,0728.56。拍立得缓缓吐出的照片被夹进记录宝贵见闻的红绒面册子里,我把它捂在心口,而后静静地看着那些展品,仿佛在看一条曾经波光粼粼、如今却停滞凝固的、历史的河流。
我突然想起楼兰壁画上剥落的朱砂,想起顾恺之《女史箴图》上东瀛收藏家的钤印,想起天龙山佛像脖颈处整齐的切割痕。玻璃展柜里的温度计恒定在20℃,却冻住了所有关于故土的记忆。当那个小男孩指着龟裂的漆器问“它们会想家吗”,我忽然听见万千文物的呜咽在穹顶下共鸣。
它们漂泊四海,应该比此刻的我更想回家吧。
暮色中的特拉法加广场华灯初上,我抱着红绒面册子坐在石阶上。霓虹灯牌在纳尔逊纪念柱上投下变幻的光影,恍惚间,那些光斑竟拼凑出李和临终前描绘的场景——某个霞光万里的清晨,修复完成的龙纹瓦当将被重新安置在故乡的庙宇之巅,釉色里的云母仍在等待真正的朝阳。
见习编辑:郑欣宜
责任编辑:周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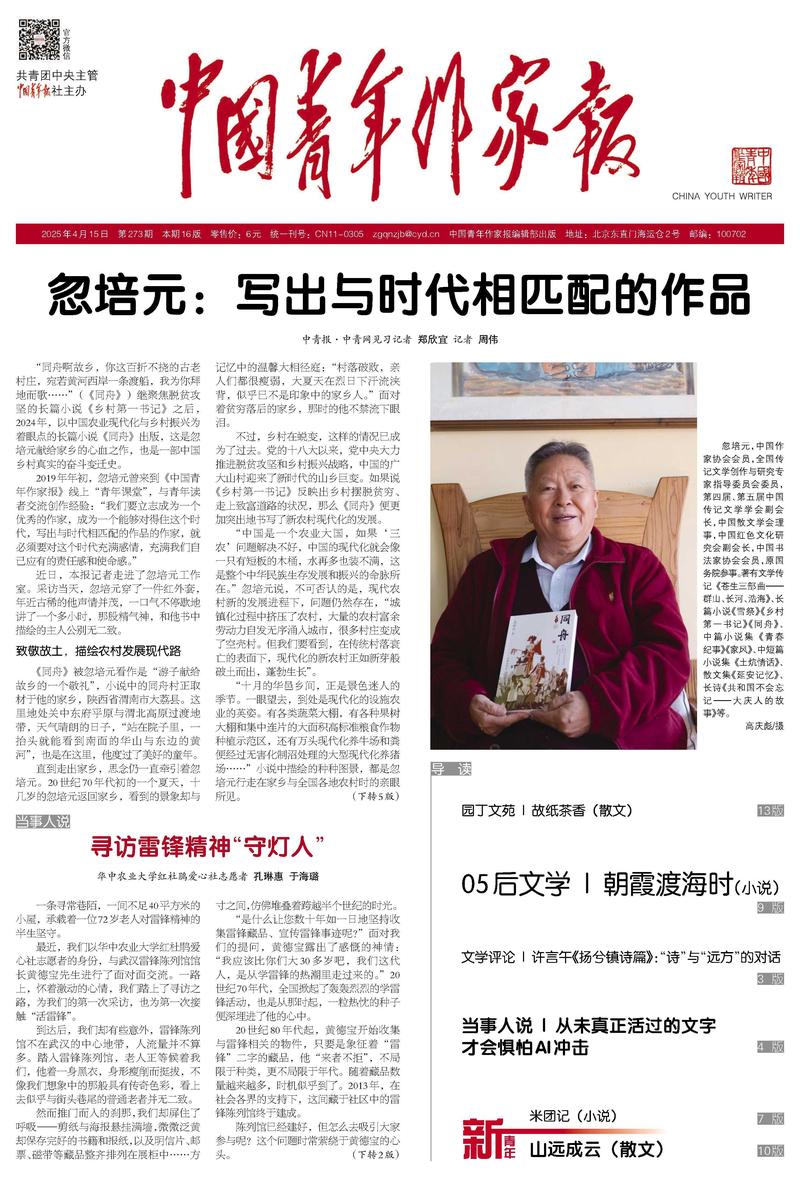






 放大
放大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