梧桐巷的日头总是起得晚些。老陈趿着塑料拖鞋走到巷口时,油条摊的青烟刚漫过灰瓦檐角。王阿婆的竹簸箕里躺着20根油条,金灿灿的,像列队晒太阳的胖娃娃。对门李奶奶正在封煤炉,白烟顺着铁皮筒爬上屋檐,惊得歇脚的家雀扑棱棱飞进晨雾里。
“今朝的面发得软和。”老陈捏着油条尖儿,看蜂窝似的面筋在晨光里舒展。王阿婆舀了勺豆浆递过来:“你倒清闲,巷尾张家的后生这个点都挤3趟地铁了。”话音未落,布帘下钻出个黄毛团子——米团是上个月在垃圾箱后头捡的,发现它的时候正抢食半截玉米棒,如今养的是油光水滑,脖子上的铃铛晃出一串清音。
日头爬上水杉树梢时,米团开始扒拉老陈的裤腿——该准备午饭了。火腿肠要切成丁拌粥,鸡蛋黄碾碎了撒在表层。杂货铺老赵扒着门框笑:“你这狗吃得比人金贵。”话没说完,米团蹿出去追野猫,撞翻了修车铺的黄油罐子。
卖菜的张婶挎着竹篮经过,篮里青椒还沾着露水。“正经事不做,倒当起狗爹来了。”她朝藤椅努努嘴。老陈呷着茶,看茶叶梗在滚水里浮沉,“您这辣椒该摘晚两天,日头再晒晒才出香。”米团突然竖起耳朵,邮递员的自行车铃正叮当响过青石板路。汇款单照例是女儿寄的,边角沾着米团亮晶晶的口水印。
蝉鸣最黏稠的晌午,裁缝铺的收音机飘来股票行情。米团蜷在藤椅下啃拖鞋,尾巴扫得砖缝里的野草直晃。老陈数着槐树影里的光斑,想起厂子倒闭那天,车间主任的老怀表也这么晃啊晃的。忽然米团蹿出去狂吠——自行车碾过巷口的窨井盖,小周扔下包裹就跑,衬衫后背洇着汗渍。“喝碗凉茶再走?”老陈喊了声,自行车又撞翻井台边的空花盆。
日子像井台上的青苔般静静生长。米团渐渐通些人性:收废品的板车轧过门坎,它就龇牙咧嘴地叫;见着挎菜篮的街坊,尾巴摇得能扇出风来。有回老陈在躺椅上打盹,这小崽子竟把他的老花镜叼进了里屋,塑料镜腿沾着火腿肠碎屑。老周见了直咂嘴:“该送去读警犬学校!”
中秋那日,女儿带着外孙女回来时,云絮正往月轮上缠。小丫头追着米团满院子跑,碰翻了檐下腌萝卜的陶瓮。“不碍事。”老陈捡起块萝卜在井台冲洗,“你妈小时候打碎过整坛醉蟹。”话音未落,米团突然冲着对门狂吠。李奶奶家的煤炉青烟袅袅,混着桂花香往人鼻子里钻。女儿瞪他一眼,转头去哄哇哇哭的孩子:“爸,您少提那些陈芝麻烂谷子。”
后半夜落下了雨。米团挠门的声响混在雨声里,爪子刮得门板吱呀响。老陈披衣起来,见李奶奶家的浓烟顺着门缝往外渗,像条扭动的大蟒。等叫醒人收拾停当,布鞋已经湿得能养鱼。米团抖着毛上的水珠,喉咙里发出得意的呼噜声,惊得瓦檐上的雨水串成珠帘。天蒙蒙亮时,李奶奶送来一罐酒酿,瓷罐上还留着煤灰指印。
深秋的梧桐叶打着旋儿往护城河飘,老陈夹着本《扬州画舫录》往家走。卖包子的崔阿婆正在收摊,竹簸箕边缘的油渍映着夕阳,泛出虹彩。“米团呢?”她朝巷子努努嘴。但见那黄毛团子正追着穿西装的年轻人跑——正是上月蹲在柳树下哭的那个,如今皮鞋擦得锃亮,领带却仍松得像腌菜。
夜风送来木樨香时,女儿那句话和月光一起漏进葡萄架:“爸,您现在这样……其实挺好的。”老陈正给米团梳毛,梳齿间带起的绒毛浮在光柱里。隔壁老周荒腔走板的梆子戏飘过来:“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哪——”惊飞了瓦檐上打盹的麻雀。
霜降那日,米团在院子里刨出个铁皮盒。里头装着玻璃弹珠、生锈的铜钥匙,还有张泛黄的厂区合影。老陈摸着照片边沿的锯齿,想起20年前那个暴雨之夜,他抱着纸箱站在熄了灯的厂门口,雨滴把“安全生产”的标语洗得发亮。米团忽然用湿鼻子碰他手背,远处飘来烤红薯的焦香。
冬至前的头场雪落得悄无声息。老陈给藤椅绑上棉垫时,发现扶手的塑料绳结里还卡着半粒西瓜籽——是今夏和米团分食的那颗。王阿婆的油锅又开始滋滋响,新炸的猫耳朵甜香混着雪粒,在梧桐枝头结成晶莹的霜。米团蹿出去追雪片,铃铛的清音撞碎在晨雾里,惊起竹簸箕里20个金灿灿的太阳。
见习编辑:郑欣宜
责任编辑:周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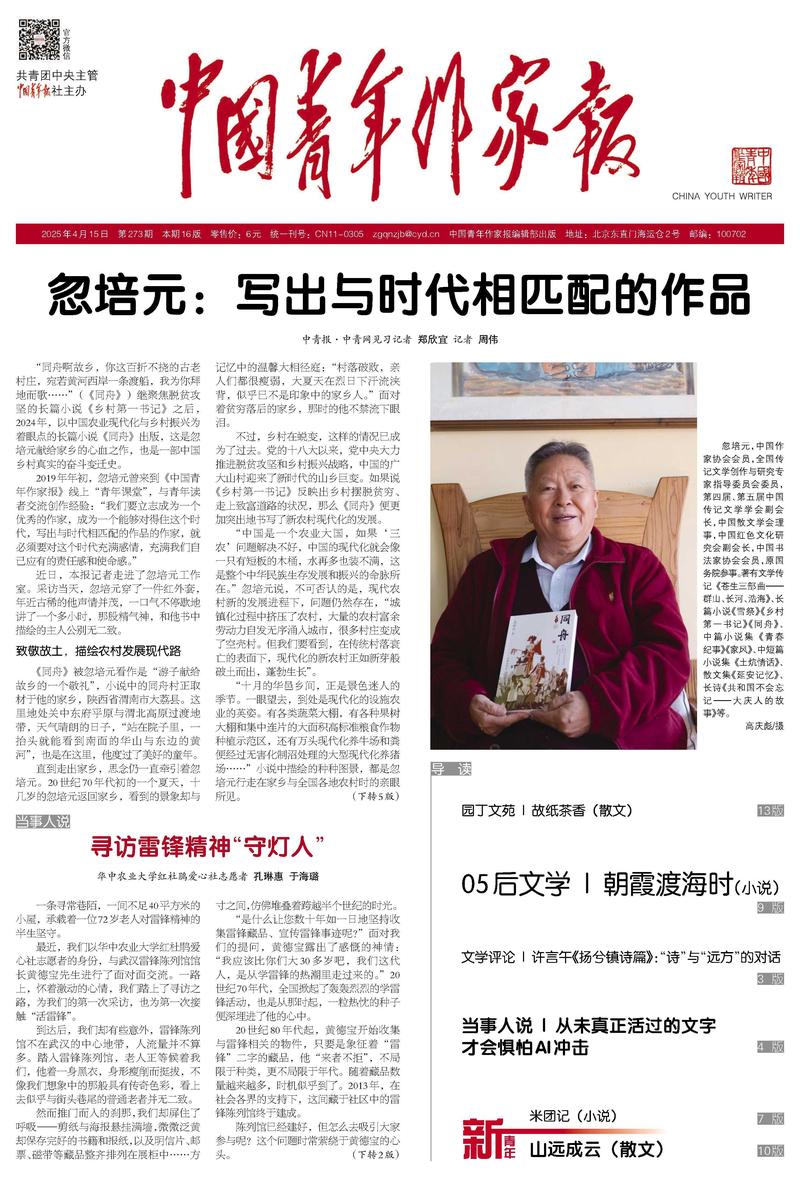






 放大
放大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