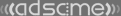我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已经是30年后了,或许是我走进他们的生活有些晚了。
这个故事还得从剧院说起。从小在戏班子里的孩子,打打闹闹,衣食住行没有一点离得开舞台,晚上台上练功,累了睡在台下,我师爹就是这样一个孩子。
因为父母都是戏曲演员,他从小被耳濡目染地沾上了戏。原本想当演员的他被师爷爷的一棍子打了回来。不唱戏就没有活路,不唱戏也就遇不到师娘。
那时还是宿舍楼,大清晨太阳还没出来,小一辈的演员就已经在楼下喊嗓子了。师娘只是开声的几嗓子,就把师爷爷和师奶奶引了过去,两个人挤在阳台的窗户边,用眼睛挨个看楼下的小姑娘,终是让老两口找到了。自那时起师爷爷就一直说:“这个姑娘是个唱戏的好苗苗,要是来了咱家该多好。”
不久就赶上了戏校的考试。师爹铆足了劲儿,几乎见天去作为考官的师爷爷那里走动,旁敲侧击地说,他谈的女朋友就是这次要应考的一员,希望师爷爷能通融一下,给个高分。
虽是这么说,那女生却不知何名何姓,且师爷爷一向公平公正,便一棒子把师爹又打了回去,让他想都别想,去让自己的女朋友拿实力说话。
到考试这天,师爹在底下看着,师爷爷的刻意压分让师爹手心里总攥着把汗。但最终师爹一直目不转睛地看着的小姑娘还是拿了第一,师爹攥着的手也松开了。
“扮相秀丽俊俏,唱腔圆润甜美,表演声情并茂,张弛有致,颇有戏缘。”这次考核的第一被师娘拿下了。赛后师爷爷才知道,这个被他压低分还拿了第一的小姑娘,正是他探着头找的楼下的女孩。
但当师爹和师娘一起出现在大家面前,亲友对师娘的不认可也随之而来:一个村里来的小丫头,怎么能嫁到这样的戏曲世家里?
也巧,赶上师爹被派去北京学习,一走半年,师爹从车窗里和她打招呼,那绿皮火车越跑越远,只留下她一个人在站台上张望。
师爹喜欢吃包子,师娘就特地在他走之前让他饱吃了一顿。那时候没有油烟机,包子一上气,打开锅盖的那一刻,厨房都是热腾腾的蒸汽,师娘就站在这氤氲里。到现在说起师娘的包子,师爹只说念的不是包子,是当时蒸包子的人。
“我爱你。”“我真的爱你。”“我很爱你。”一封信没几句话,可是一天时间却能从北京邮来三四封。师爹说自己没什么文化,那就用最简单的方法表达自己的情感。几年前师娘收拾办公室,还找到一堆师爹当年邮来的信。半年里,这样的信没断过,师爷爷和师奶奶对师娘的喜欢也没断过。
1989年,师爹和师娘办了婚礼,他们在一个剧团上班,在戏里戏外都是夫妻,总在互相挑刺,找工作上的毛病,“笑了恼了又好了”成了家常便饭。后来他们同排一出《高君宇与石评梅》,大才女石评梅和革命先驱高君宇在幻境的烟雾弥漫中重逢,台上的师娘和那时站在厨房里的师娘一样。
一晃都30年了,师爹和师娘的爱情也一直是这样,虽然生活中不免磕绊,可总有一个人退一步。师娘说,老了之后就怀念从前的事,怀念当年和师爹一起在汾河边上遛弯、说戏、练功。这话被师爹听了去,自那后每天早上汾河边都有两个人拉着手,沿着汾河慢慢地走。
责任编辑:曹竞 王诗瑶 毕若旭

 上一版
上一版





 放大
放大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