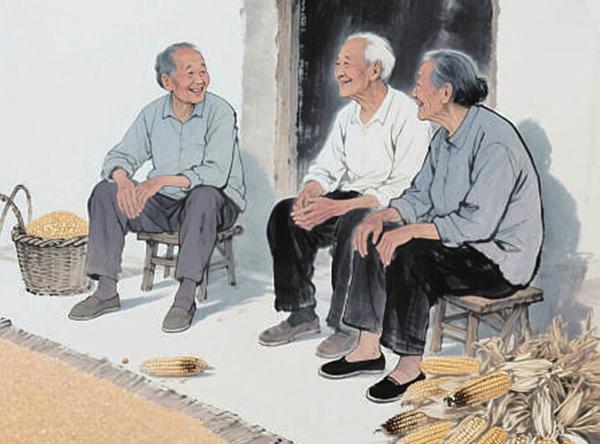
这几天阿林时不时就和阿金说要回去,还把在城里认识的老人的家几乎都走了个遍。阿金想着,兴许是老人家一时兴起,玩性大发,想找老友叙叙旧。但他这样东跑西跑,让阿金不免有些担心。
父亲已80岁高龄,总怕一个小意外就剪去人生的末端。
家乡的称呼,都习惯在名字里取一个字,前面加上“阿”,简单好记又显亲切。阿林是大家对阿金父亲的昵称,他也习惯叫父亲“阿林”。
“阿金,这个周末你不是休息吗?带我回去看看。”阿林又一次提起回老家的事情。
那是阿金和父母亲生活了几十年的老屋子,是砖瓦和木头修筑起来的双层阁楼。屋子在离县城30分钟摩托车程的小山村里,安稳地扎在半山腰上,到饭点准时升起柴火的薄烟。
后来阿金进了城,在那组建起家庭,周末会把阿林和母亲桂琴接去城里住,但他们总是没住几日,就说不习惯,又匆匆背起旅行袋回村子去了。阿金有时和妻子说起这件事,总会调侃道,老屋子才是他们老两口放心不下的孩子。
前年,菜园边的那棵野枇杷树终于不结涩果了,结出一批甜的枇杷果。桂琴说这是个好兆头,可以讨个圆满的意味,就把这果子都给摘下,在濯菜池里一颗一颗洗净,放在红色果盘里,端去供奉保生大帝,点上3支香,口中念念有词,摔了一次茭杯,结果是一正一反。桂琴很是欣喜,人老了以后总是不太容易笑,这次桂琴由内到外都透出一种柔和而愉悦的光,阿林感觉桂琴好像回到了他们青春的那个年纪——从裁缝厂下班回家的桂琴,梳着两支麻花辫,穿着花布衫,对在厂口等待她的阿林羞涩地微笑。
那天,桂琴新做了一碗猪油,炒了空心菜,煮了鸡汤。她在饭桌上乐吟吟地回忆起他们挖野菜和领粮票的时日。一个月没用的染发膏被桂琴从水池下拿出来,阿林看着桂琴涂染发膏,黑色塑料梳掉色了,这次又沾上染发膏的颜色,看上去就像着色不均匀的头发。今天桂琴涂得很仔细,一点一点把膏体抹在头发上,空气中飘着熟悉的气味。发丝从梳齿间筛过,一下就流走。
阿林隐隐感觉到什么,这和烟星子一样的时光似乎马上就要熄灭。
第二天桂琴没有醒来,手轻轻地搭在阿林的手臂上,头发还散发着染发膏的香味。阿林感觉酸涩,果子昨天祭拜完就放在他们的床头桌前。
桂琴的老人机昨晚还在充电,和阿林的老人机静静地躺在一起。阿林抓起老人机,拨通了通讯录里的第一个人,桂琴的电话响起,显示“阿林来电”。手机铃响了几回又沉寂,阿林终于挂掉,拨通儿子的电话,说,你姆(母亲)走了。
出殡的时候要从山腰绕一圈,一直到山脚下。考虑到阿林年事已高,又怕老人家伤心过度损了气,来送葬的亲戚都说他走一段就行,不用走完全程。阿金知道阿林哪里肯,只特地嘱咐殡仪队的人走得再慢点,吹的哀乐也再慢点。
白花在竹林里飘荡,魂一般,兜兜转转还是坠回土地里。唢呐声里偶尔掠过杜鹃的一啼。走山路的时候阿林没有哭,头脑里全是昨天的桂琴,他努力回想她有没有不经意提起的遗憾。桂琴的姐姐走后的三四年里,桂琴总在梦里哭,阿林轻轻拍醒她,倒了杯白水,说吃吃水。他们在清明节时,会给先祖和过世的亲人烧香,送上天地银行的钞票和制作精美的纸衣。这里的栀子花开得很早,雨落后就冒出小巧的几朵白花。一阵鞭炮响息罢,折朵花,倒上茶,也就轻声细语地过去了。
几日后,阿金把阿林接去城里和他们一起住。阿林心里膈应,但也不好说什么。
回老家这天,他们一大早就出发了。
回去的路上,阿金特地摇下了车窗,父亲像孩童一样,目不转睛地盯着每一处闪过的场景。村子新建了路,多养了些鸭,猪棚少了很多,香蕉正青。
“午夜无伴守灯下,清风对面吹……”阿金调小音乐声。阿林已经有些耳背,或许并没有注意到这个变化。
碾过一段石子路,竹叶沙沙响的地方就是他们的家。
阿林下了车,挪着步就往他和桂琴的房间走去。屋子没有落下太多的灰,常年使用雪花膏的香气还弥留在房屋缝隙里。他们结婚用的那块红枕布已经褪色,破处缝补又开线,最后就剩下一层粉色的里子。
以前囤下的柴在时间里潮湿。
阿林开了水龙头,从抽屉里搬出茶具,颤颤巍巍地站在濯菜池前清洗。
阿金说,阿爸,我来吧。
这套茶具,他们去年回来的时候也洗了一次。那时阿林坚持要自己爬梯子,说要给老房屋的屋顶清理一下,雨后的泥土松软,梯子没有站住脚,他从梯子上摔下来,昏迷了几天,睁开眼的第一句话是,阿金,你怎么长这么大了。那时,阿金站在床边,看着父亲像小老鼠一样,蜷缩在被褥里。
第二句话是,阿金,桂琴对我说“无代志”(闽南语,意为没什么大事),会没事的。
第三句话是,我要吃茶。
阿林又从厨房移出一壶酒来。用大木塞塞着,是泡了30年的酒,阿林之前一直不让阿金喝。
阿金感到奇怪,阿爸今天怎么这么大阵仗,又是茶又是酒。
远处人家的公鸡啼开一嗓,阿林问:“怎么没听见永贵的摩托车声了?”
永贵是村子里卖猪肉、鸡鸭肉的屠夫。村子循山势,错落开来,零星散着,离县城又远,每户人家几乎都要靠永贵来送肉。每天鸡一打鸣,那台老式柴油发动机就会发出“突突突”的声响,阿林也总会提早起床,站在门前空地,等着永贵来送肉。有时不需要肉,也会守在门前,问候几句。
正是父亲摔倒的那段时候,永贵也走了。亲戚们都怕阿林再出什么差错,也都和阿金一起瞒着这事。
阿金开口道:“走了。”轻飘飘的,和着风被吹进山头的雾。明明声音那么轻,阿林却听得真切,自从他意识到真的老了以后,不断地有人走了,走了就走了,一去不复返。
阿林点了点头,似乎叹了口气,又似乎没有。但阿金总归觉得阿林是叹了口气,或许是在心底。阿林起了步,牛皮凉鞋在沙地上摩擦,簌簌地发出微响。他又转过身来,问道:“什么时候。”
“三月初一。”
“哦……”阿林低闷一声,“种地瓜的时候,害冷。”说罢沿着土路向下走去。
“阿爸,去哪儿?”阿金放心不下,几步跟上了阿林。
“买包烟。”
阿林摔倒后就戒了烟,尽管看到烟草柜台里摆放的中华烟还是忍不住多看几眼,但还是背着手走开了。阿金默默跟在父亲身侧,或许是去吴姑的小卖部。
鸡鸣再一次响起,水波般荡在山壁间。那是禽鸟的骄傲,太阳和人们由它们唤醒。
吴姑抱着熟睡的孙女从房门走出来,无须打理的齐耳短发似乎是农村妇女转变为“阿嬷”的标志。她腾出一只手往沙地里撒了一把米,几只鸡“咯咯”疾奔到她的脚下。养了十几年的大黄狗已经没法围着吴姑蹦跳讨要吃食,它低哼了一声,又趴下了头,尾巴甩了几下,以此问好。
“阿林。”吴姑很是惊讶,拍掉手里黏着的几粒米,原本散开的鸡又扑棱着翅冲过去。
阿林点了点头。吴姑笑道:“阿林回来啦,气色看起来很好,快进来坐。”一个晃动,把怀里的孙女惊醒,孙女“哇”的一声,哭了起来。
“仔儿不哭,仔儿不哭,阿嬷给你唱歌。”吴姑常年劳作的手臂结实有力,环着孩儿的时候却像捧着云似的轻缓柔软。
“天乌乌,欲落雨。阿公拿锄头,要锄芋头。”乡音像大地的土,铺在仔儿的心里。
吴姑一边轻声哼着,一边招呼阿林走进小卖部。
“都有孙女噢。”阿林看着小小的仔儿吮着手指,笑着说。
“是哎,老了,老了。”吴姑熟练地拉开烟草柜,抽出一包软装中华。
“几多钱?”
“不用,这么久才回来,送你吃烟。”吴姑摆摆手,出了小卖部,又要向一旁的厨房走去。
“吃茶不?”
“免啦。”阿金站在不远处,看阿林摆摆手,应该是要回家的意思了,这才赶上去搀扶。
“吴姑!走啦!”阿金朝厨房喊了一声。
“哎!阿金!款走(慢走)啊!”
听说阿林回来,隔壁的阿香嬷一家从县城驱车下来,热热闹闹地办了桌午饭,炒笋,巴戟天排骨汤,还有特地从县城带下来的杨记熏鸡和金山拉面。阿林开了酒,糙米的香气漫延整个堂间,饭桌上说着祝福的话,饮进了许多杯。阿林有些醉了,脸色涨红,巍巍地站起来,把着酒杯往空气中一推,夸阿金孝顺懂事、事业有成、家庭美满。又饮下一杯,唱着“酒干倘卖无”,一曲罢了,猛地瘫在靠背椅上,眼泪沿着脸上的褶皱一卡一卡地滴下来。
阿香嬷也和阿林一般醉,和着阿林呜咽。
座上的年轻人都有些窘迫,两位老人家哭了。缘由大抵是知道的,记忆和年龄总是逆生长,人越大,记忆越年轻。但又是不知道的,其间百感交错,又何况人人的百感又不尽相同。
午席结束后,阿林被背到房间里休息。阿金给阿林泡了茶,就放在桌上。风从木窗子的缝隙挤进去,刮起白芽奇兰的茶香钻进阿林的鼻腔。
阿林又梦见桂琴了,这次还多了永贵。永贵来家里做客,桂琴刚从灶台出来,还没来得及解下围裙,就坐了下来,喝上一杯阿林泡的茶。永贵问,今年竹笋卖了多少?阿林说,比故年多了点。永贵打趣说,本命年好福气哟。阿林放声大笑……
夜半,阿林醒过来。
月光照满堂,阿林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平静。
他起身披了件外衣,木床咯吱咯吱发出古旧的声音。阿金已经把茶具洗好,摆放在走道边,月光恰好照着,还没蒸发的水珠反着光。
今天阿金刚好买了大饼,就放在堂厅。阿林搬起茶具,摇摇晃晃穿过廊,披着夜里的露气踏入堂厅,稍感冷意。大饼是他小时候最爱的食物,只有在重要的日子才能吃到。饼里混着猪肉馅,冬瓜条和花生仁,表面印有红色的“福”字,擦着一层薄薄的猪油,喷香喷香的。阿林翻出个盘子,把饼切成小方块,整整齐齐地摆放好。热水倒入茶壶,腾起的水汽在斜进的微光里若隐若现。
阿林给自己倒上茶,一口一口抿。
他拿起一小块饼,含进嘴里。饼渣在口腔里化开,咸咸甜甜。
他忽然觉得空气有点涩,像生水一样流进记忆,洗去灰黄的尘。所有瞬间像蒲棒胀开了絮子,飞向阿林。
从母亲送他上学开始,缝补的书包,到遇到桂琴的那天,到和桂琴拍证件照的那天,到生下了阿金,再到他抱上了孙女……然后桂琴去世,然后他去了城里,然后他又回到了这里……
还漏了什么东西。某个念头引着他站起,直向菜园走去。
枇杷树枝叶弯弯,他摸着树干缓缓坐下,鹅仙山就他对面,寂静地立着。枇杷花落了满地,像月光的薄片吹下来。他把手伸向垂下的树枝,摸了摸,果皮挂了凉气,摘下一颗,剥去外皮,汁水沁进舌咽。
桂琴笑着说,一定是好兆头,讨个圆满的意味。
阿林倚着枇杷树,粗粝的树纹压住他落去毛发的头,他全身都变得柔软,一如出生的婴孩。天淡了,阿林想,什么时候鸡鸣呢?
山谷荡起鸡鸣。
阿金点的香静悄悄飘了出去。
责任编辑:曹竞 毕若旭

 上一版
上一版





 放大
放大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