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90年,我出生于一个川东的小山村,村子陷在两座大山的山坳里,没有超市,更没有商场,就连唯一通往外面的道路都是山石子儿铺就的,并不规整,一到雨天就坑坑洼洼,连堂屋的大门都不想跨出去。
村里唯一的小学是砖瓦砌成的,夏天的时候很是凉快,可一到冬天就冷得直打哆嗦。孩子们除了拥有几本课本外,几乎不曾有过任何的课外读物。这个小山村是没有报亭书店的,更别提图书馆了。上课时,孩子们昏沉地听老师讲课;放学后,虽不像城里孩子有许多的精彩活动,但玩耍的花样也不枯燥。女孩子喜欢跳格子、跳橡皮筋、翻花绳、扮家家;男孩子爱滚铁环、打弹珠、摔泥巴炮、下河洗野澡,或是漫山遍野疯一样地跑。
我们男孩子干过许多的坏事和傻事,为留点面子,就不一一赘述了,举一例足矣。在祖辈那个年代,像这样的偏远小山村,男人讨不到媳妇儿是一件极其普遍的事情。我们村就有好几个,大人们都戏谑他们“光棍儿”。其中有一个光棍儿的年纪和我爷爷差不多,守着一个公共院坝,整天无所事事,靠帮村民们看管谷物换一口饭吃。男孩子经常跑到院坝里去把晾晒的玉米和谷子踢得乱七八糟,气得光棍儿抄起棒棍就要开打。在“光棍儿拿棒棍儿,一蹶一拐笑死人儿”的此起彼伏的嘲笑声中,光棍儿追得我们满院坝跑,结果往往以光棍儿气喘吁吁地坐在田埂边,气愤又无奈地骂上两句作为结尾。
如今回想起来,当年的我们做的不仅是一件傻事,更是一件坏事。事后好长一段时间,都不见光棍儿的身影。母亲说,光棍儿他脾气大,一个人宁愿跑城里去要饭,也不愿再给咱们看粮食了。好几个学期我都不曾见过他了,大人们摆的龙门阵里也开始没有了他。我长大了许多,不再调皮捣蛋。再后来,家里买了台背投电视机,动画片遂成了我的最爱。整天幻想成为一名“光能使者”,吼着“一刀两断,如意神剑”去解救全世界。世界没被我解救,我却因为撞断了电线杆,差点被母亲打得需要被解救。
日子过得就像家门外的那口老井,看不出有啥变化,水却早已换了又换。渐渐地,我也把他给忘了。
二
再次见到他,是在五年级下学期。一天放学后,赶着回家看《光能使者》的我,路过公共院坝,看到一个佝偻的身影正在倒腾杂物。不知为何,我竟然欣喜若狂地朝着这个熟悉的身影喊了声“光……”,又下意识地闭上了嘴。他听到了我的喊声,朝我的方向看了过来,笑了笑,豁了口的模样甚是滑稽。我也朝着他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
只见他佝起身子,在一辆破旧的三轮车里翻来翻去,然后朝我举起了一本书,挥舞着抬得并不高的手臂。我忙从山石子儿路上跃进豌豆地,跨进院坝,跑到了他的身边。他把书递到我手上,说是“连环画”。什么画这么小?他呵呵地笑出了声,搬起一张太师椅对我说:“你就叫它‘小人儿书’吧!”小人儿书?对,可不就是小人儿书吗?跟我的巴掌差不多大的小人儿书。
那天,我错过了最新一集的《光能使者》,但我看完了人生中的第一本课外读物——《大闹天宫》。见我躺在太师椅里赖着不走,他朝我歪了个嘴,使了个眼色,我看见堂屋的门槛旁立着个大口袋,鼓鼓的。从未与他有过默契的我,那一刻竟然心领神会地拔腿就扑了过去。直到山色渐晚,母亲站在山石子儿路上唤回家吃饭了,我才依依不舍地放下手中的《武松打虎》。
晚饭时候,母亲问我跑去了哪里?我说我一直在公共院坝。母亲瞪着大眼看着我,光棍儿回来了?时隔几个学期,再次听到母亲叫他“光棍儿”,我一脸嫌弃地不乐意了,他不叫光棍儿,他也没有去城里要饭,他是去收小人儿书了。母亲见状,立马改了口。我就把在院坝看小人儿书的事情都一五一十地说给了母亲听。母亲也不打断我,待我说完了,看向父亲,他究竟叫什么名字啊?对于母亲竟然不知晓这事儿,我很好奇。母亲却说,她嫁过来的时候,大家已经都管他叫“光棍儿”了。我也很想知道他究竟姓甚名啥。正在扒饭的父亲抬起头看了看母亲,又看了看我,回了句“我也不晓得。我小的时候,他就是‘光棍儿’了”。见没得到想要的答案,母亲有点怒了,你都不知道,还有谁知道?
还有谁知道?爷爷呗。爷爷在哪?后山躺着呗!
三
我经常往他家跑,无论刮风,还是下雨。母亲说,喂猪都没这么勤快的。好在也不阻止我。
每次看到他从城里回来,我就迫不及待地冲上去翻他的三轮车。他也不恼,还夸我。他主要靠收荒度日,破铜烂铁,塑料纸板,只要能收的,都收了去卖钱。只有一样是舍不得卖的,那就是各种各样的小人儿书。《小城之春》《上甘岭》《小兵张嘎》《崂山道士》《三谒碧游宫》《曹爽伐蜀》《济南相》……他家的书实在是太多了,我便给他取了个外号——书爷爷。他也乐呵我这么叫他,我一叫,他就笑,一口叶子烟就像一个小烟囱一样冒了出来,呛鼻得很。
许多的日子,我都在他家的太师椅上度过的,常常一躺就是一整天,连午饭都在他家解决。有时候太阳都下山了,我还窝在太师椅里看我的小人儿书。这时候书爷爷就会走过来侃我,你是真的看进去了?还是想赖着不走继续吃我的萝卜干儿啊?
有时候我会傻笑,吃了走也可以啊,我肚子小,吃的又不多。有时候我装作没听见,继续看我的小人儿书,因为我知道书爷爷会给我萝卜干儿吃的。有时候书爷爷会拍拍我的小脑袋,歪着脖子看书不累吗?哪天近视眼了,啥都看不清,整天戴着两个玻璃片儿,造孽得很哦!我却不在意,还反嘴,我眼睛好得很。然后指着院坝外面,你看,张婶儿家的土狗儿又在糟蹋豌豆了,那么远我都看得清清楚楚。豌豆地是张婶儿家的,书爷爷还是被吓得抄起个棒棍就往外跑,佝偻的身子一抖一抖的,凸起的后背一耸一耸的,惹得我在太师椅里哈哈大笑。知道自己又被我骗了,书爷爷气得扔掉棒棍拿起扫把就要打我,我不和他打,也不让他打着,我俩就在院坝里跑来跑去,不像打骂,倒像是在玩追逐的游戏。嬉笑声传出了院坝,顺着山石子儿路,传到了山顶上,扰得山雀儿不得安宁,扑哧扑哧地往天上飞。
四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后来,我真的戴上了玻璃片儿。为这事儿,书爷爷数落了我好几回。
不过,我也做了一件让书爷爷倍感高兴的事情。那就是在刚上初中的时候,我的随堂作文被语文老师当作优秀范文在全班朗诵。书爷爷听后,皱纹笑成了一朵花,摇着母亲送的蒲扇,一个劲儿地自夸,看来我的这些小人儿书还真是有用啊!
升入初中后,我去到了镇上求学,一周回家一次,每次回家我都会直奔书爷爷家,去看新收回来的小人儿书。我会给书爷爷讲镇上的故事,人很多,街很大,讲早就读过“鲁智深倒拔垂杨柳”的故事,讲作业越来越多,瞌睡总是不够。一听我上课会偷偷打瞌睡,书爷爷就会凶我两句,你以为学校是我家啊,想怎么睡就怎么睡?说罢,挥了挥手里的蒲扇,指着太师椅说,那儿,去睡吧!
再后来我去了城里,就是书爷爷经常去收小人儿书的那个城里。我读的是封闭式高中,一个月才能回家一次,平常都是三点一线,一到周末就和同学们请假出校门压马路,城里的许多地方都留下了我们的脚印。
成长,就像走路一样,走得多了,就误以为自己长大了。有一次我在一个商场门口撞见了书爷爷,书爷爷拖着那辆破得叮当响的三轮车朝我走了过来,微笑着递给我一本《木兰从军》。在同学们异样的眼神中,我把书扔到三轮车上就跑开了。我知道自己做得不对,可那个时候的我,不愿让同学们知道我和一个收破烂的老头子有什么关系。
人与人之间,彼此拥有默契也不见得是一件好事情。这件事后,我又遇见过书爷爷好几次,可我们都默契般地装作不认识,即便迎面撞上,也不在同学们面前露出一点儿蛛丝马迹。几次下来,我的内心实在是备受煎熬,憋不住了,就把这事儿说给了母亲听。母亲说,爷爷大度着呢,不碍事儿的。古有负荆请罪,今有蒸蛋赔错。在母亲的劝说下,我给书爷爷端了一碗蒸蛋过去。书爷爷啥也没说,笑呵呵地就把满满的一碗蒸蛋吃进了肚子,还一个劲儿地说,这比萝卜干儿好吃多了。
五
书爷爷去城里的次数越来越少了,收回来的小人儿书也越来越少了。有时候去城里一趟,一本都没有收回来,即便收回来一本,也不如学校图书馆里的书好看。
渐渐地,我鲜少再拿起书爷爷家的小人儿书了。每次回家,我还是会往书爷爷家跑,给书爷爷讲学校图书馆有多大,有多高,有各种各样的书,怕是一辈子也看不完。《茶花女》《巴黎圣母院》《追风筝的人》《动物农场》《死魂灵》……这些经典的外国名著,书爷爷家里都是没有的。我把我看过的书都说给书爷爷听,书爷爷也不说话,窝在太师椅里一呼一吸,有时会搭上两句,有时干脆一言不发,甚至有一次,他竟然在我说得兴高采烈的时候睡着了,害我浪费了好半天口水。对于书爷爷此等态度,我一点也不高兴,转过头就把这事儿说给了母亲听。
书爷爷怎么能这样啊?我给他分享我的故事,他却睡着了!
爷爷年纪大了!
他的年纪一直都很大啊!
爷爷是快“老”了!
……
快“老”了?当年爷爷也是“老”了才去后山的。母亲的意思是,书爷爷也要去后山了吗?母亲叫我走之前多去陪陪书爷爷。
我去的时候,书爷爷仍然窝在太师椅里,闭着双眼,一动不动,就像小时候的我一样,将整个身子都凹了进去。我把带回来的作文念给他听,告诉他,我在全国征文比赛中获奖了。他微微张了张嘴巴,抖了几下,像是要跟我说些什么,却半天没说出来一个字。
我跑到厨房打了点水,在他干瘪的唇上抹了几下,凑近他耳朵说,都是书爷爷您的功劳!书爷爷还是一个字都没吐出来,嘴巴抖着抖着就笑了。我知道他听见了我说的话,也听懂了我一直想说、却碍于面子不敢直言的那句“谢谢”!
书爷爷“老”了,在我回校的第二周。青石板是村里的石匠一锤子、一锤子打的,棺材是母亲叫人从镇上拖回来的。母亲叫我裹上一袭白方巾,端着灵位走在出丧队伍的前面,在村民们的簇拥中,将书爷爷抬进了后山。
第二天返校,母亲给了我一个包裹,一块皱巴巴的麻布里躺着一本小人儿书。母亲说,爷爷把一屋子的书都捐给了村里的小学,只留了这一本,说是留给我的。不管以后去到多大的城市,也要记得回来。那一刻,憋了一天一夜的眼泪,再也止不住了,我抱着母亲大哭了起来。
多年后,那本《木兰从军》仍然跟随着我,我带着它去了省城的大学,去了大理的洱海,去了上海的外滩,去了北京的故宫……去了许许多多地方,但我仍然选择在一段旅途之后回到故乡,回去看看荒草覆盖的院坝,看看愈发葱郁的大山,看看山腰处的书爷爷,看看已为数不多的乡亲们,看看生我养我的小山村。书爷爷说过,埋着亲人的地方就是故乡。
责任编辑:谢宛霏
杨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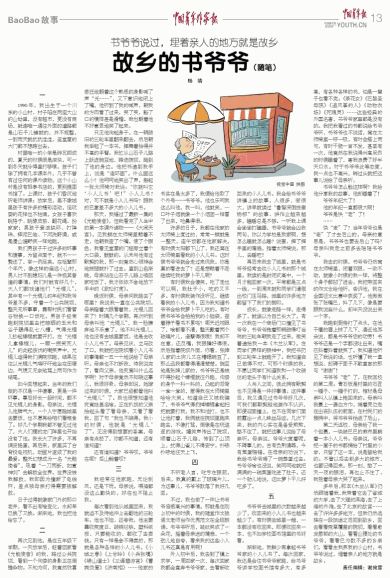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