缄默的余烬在灶门内的一隅阴影中安眠,唯有一罗灼着银光的蛛网在灶门外与之相望,相顾无言,唯有流年。
——题记
_______________
1
自年后,已经半年没回老家杜浔了。
为什么会想要回来呢?
下车时,望着异样空旷的院落四周,我便大致清楚这半年多来,这小村一角中所发生的变化。一户邻家的半毛坯小洋房告别了“平头”顶,搭起了深蓝色的铁质顶棚;另一户邻家破败的竹篱笆内,是拆了一半的三合院,还有两三堵残墙突兀而立,似乎仍存不舍;隔壁最近的一户也和记忆里有所出入,拆了栅栏,放倒了树,让狭窄的村道稍微敞阔了一些,也让那抬头可望到的天,敞阔了不少。
我本以为,唯有我家祖屋的三合院,依旧如故。
可抬头,才发现那掩藏于苔石屋顶后方的大片铁皮顶棚,即使偏僻如此,这座老宅,也依旧逃脱不了改变,无论大小,无论好坏。
而真正不变的,或许只有记忆中的它们了。
2
几年前,老宅便同它最后的一位屋主共同迎来了暮年。叔公下海务工,常年在外;他的妻子为了三个儿女的学业和家人的生计,举家搬到了村口,靠着自耕的大片土地过活;而在城市里定居了十几年的父亲和姑姑两家,也只有逢年过节才有机会回一趟老家。
“田墩自然村-73号”。跨过门槛前,我的目光在斑驳的木门旁侧停留了片刻。被风尘蚀得褐一块灰一块的土墙上钉着一块蓝白色的铁质门牌。
一块门牌,它曾无数次出现在我的视线中,在我每一次推门入院之前,都会有这么一抹蓝色掠过眼帘,但,这是我第一次如此仔细地凝视它:微微泛黄的圆润字体,掉了半层漆的数字“7”,右下角不知被谁磨花了的二维码……我本以为这块门牌的岁数要比我还大,但如此端详后,才发觉这块牌子,似乎也不过是数年前才挂上的,但在它之前呢?还有多少块我不熟识的“田墩自然村-73号”的门牌曾经被张挂于此?我没有答案。
入门右侧便是厨房,厨房外,一只灰头土脸的陶缸里依旧漾着略显浑浊的水。我知道,这一定不是从门口的那窟井里打的,那口井早在很久以前便枯透了,向井底望去,只有一片漆黑与依稀可辨的苔藓和蛛丝。
左侧是道微掩的木门,门内是不知被遗忘了多久的杂物间,我还依稀记得门里有一张破旧的木板床,但应该自我记事起,就再也没人睡过这张床了。
回首阖门,门上大片剥落的红漆上,四个蚀刻的银色大字依旧醒目,从左至右,从上及下“鹏程万里”,遒劲的字体下,寄托着的,应该是曾经的他们对子嗣、对未来的向往吧……我的手移开那锈迹斑斑的门环,指尖在那“鹏”字下端停留,确乎感受到了一丝余温。
“吱——”两扇木门在呻吟中闭合,回首,抬头,依旧是那片四四方方的天空。
跨过四四方方的中庭,迈入正堂,九十七岁的老嬷便从摇椅上缓缓起身,皱出了一副热切的笑颜上前迎接,我与父亲赶忙上前一步搀扶住她老人家。虽说已是近百岁高龄,但老嬷的身板还算硬朗,眼睛虽花,却还认得清人,耳朵虽背,却也还听得清话。甚至到了这个岁数还戒不掉烟,茶余饭后聊天打诨的时候总得来上一支,这就是我记忆中的老嬷,亦是我面前的老嬷。
3
饭后,正堂内蜿蜒着两条灰雾,也弥散着香烟那富有冲击性的味道,我招架不住,便提着相机,往院子里躲。
我迈上台阶,端着相机,思忖着这座老宅里,似乎少了些什么……是什么呢?
我登上屋顶,避开铁棚,遥望着空旷的外院,的确少了些什么。
少了那几盆本就奄奄一息却仍旧向阳挣扎的我叫不上名的盆栽;少了那只热衷于在屋里屋外四处乱窜、不老实下蛋的老母鸡;少了那几只总喜欢傲然定立在那院外破石阶上打鸣的大公鸡;少了那几只或黑或白、或肥或瘦的“扒手”野猫……
是啊,从何时起,推开院子大门前不用再躲地雷似的避开那些黏着的鸡粪;从何时起,听不到那赤冠褐羽的雄鸡声如洪钟的嘶鸣;又是从何时起,不再能于侧门旁听到门外发情野猫婴儿啜泣般的嗥叫。这些声音、气味,似乎都随着这座房屋与其主人的老去,渐渐远去了。
就好像是行将就木的她无意识地向那些昔日陪伴她的生灵们送去了告慰,无言地,与它们作别。
晌午的艳阳不知分寸地灼烧着我的皮肤,望着略微蹭上了几滴汗珠的相机取景器,我不自觉地叹了口气,转身,沿着那没有扶手且遍布青苔沟壑的石阶、挪动着宽大的厚底鞋,让自己的背影缓缓消失在了铁皮棚子的阴影下。
如此寂寞,如此清冷,这里,还能用“依然如故”来修饰吗?
4
跨越低矮的门槛,走进这间略显闭塞的厨房,我望着那张被数十年来的烟火熏得黢黑的土灶,俯身,窥向那半圆的灶门。
已然掩埋于焚化的尘埃下辨不出形体的薪柴静静地躺在灶门里,灰色的余烬堆砌而成的丘峦里不知埋藏着多少岁月的耳语。仅从这半口锅盖大小的灶门外,我所能窥见的,仅有这些沉默的灰烬,以及其深处深邃的黑。
忽而,我发现了几丝银色的光芒。那是透过方窗的阳光打在蛛网上所映出的丝线。它们盘结于灶门之外,和门里的尘埃惺惺相惜,相顾无言。
我幻想着这丘余烬向那同样沉默的蛛网诉说无尽的往事,幻想着昨日的昨日,幻想着它曾经鲜活过的每一个日月,幻想着从屋顶烟囱内蹿腾而起的炊烟……我想到了,原来,我还没来得及仔细地观摩过属于自家老宅的炊烟啊。
抬手,摁动快门,摄下一张照片,这仅仅20MB大小的图像,能为我留下什么呢?或许是我对这座老宅的记忆,也或许是曾在这里生活的四代人记忆,又或许,只是属于这方尘埃、这张蛛网的记忆。
5
合上镜头盖,回望正堂,看样子,他们的烟抽得差不多了。
我拉了一张蓝色的塑料凳,坐到了茶几边上,在与这片昏暗客厅格格不入的节能灯下掏出了手机和读卡器,开始调校起刚刚拍好的照片。
“唉哟,最近阿鑫都没来看我,说是去厦门……干什么去了?”
“集训,阿嬷,阿鑫练体育的,要去集训。”
“这样啊……那阿小嘞?小涵今年不是考完了?怎么没带他俩回来呀?”
“阿小忙着做工抽不出空啦。小涵还在填志愿,忙着嘞,过几天带他回来。”
“哦……”
……
老嬷总是惦记着她的满堂儿孙,总在默默等待着哪天大门推开,出现的是一道许久不见的熟悉身影,是她的宝贝孙子。那一胖一瘦的兄弟和他们憨厚的妹妹,是那个在儿子走后陪着自己拉扯一家老小的憨媳妇,是那个与她仅剩下的骨肉至亲。那个憨实能干的二儿子,是她的那帮越来越认不出来相貌的曾孙,是她所牵挂的每一个人儿。
但此刻,听着父亲与阿嬷的对话,听着这再醇正不过的闽南乡音,我的心底,却有一种难以名状的阵痛感。
谎。
父亲在撒谎——
那个阿小,我的叔叔,那个和父亲体格完全不同的,瘦瘦条条的明叔,早在前年秋天,便已不在人世了。
这是个善意的谎言,我明白的,正因如此,才尤外感到痛苦。
但无论是我还是父亲,抑或是她的任何一个亲人,都希望这个谎言,能够一直这样维持下去,如故……
尾声
“这样就好。”
伴随着那座饱经岁月濯洗的老宅与老人消失在那盘盘巷道中后,我如是对自己说道。
愿这里的明天,依然如故。
责任编辑:龚蓉梅
福建漳州第一中学高二(16)班 余宇宏(18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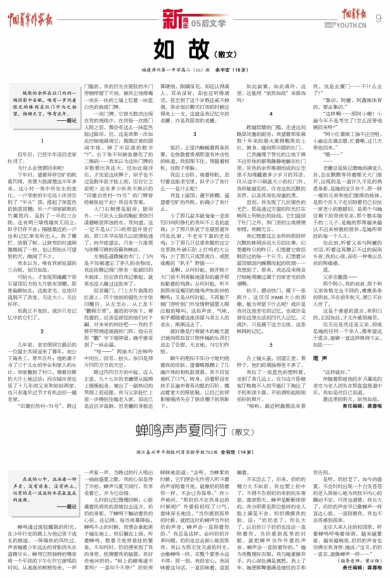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