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洛蒂曾提出“无边的现实主义”,即根据作品的特点赋予现实主义新内涵,在此命题下,现实主义能够辐射的范围显著扩大,“心理现实主义”就是其中一种,指的是“在严格遵循外部世界客观真实的基础上,加强人物的心理刻画,通过对人物心理的精细分析,去反映社会精神演变的现实”。
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善写心理闻名,尤其是《地下室手记》中的“地下室人”,几乎通篇都是心理自陈,容量相当丰富,叙事的成分则淡化至边缘。巴赫金评价“地下室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塑造的第一个“以进行意识活动为主的人物,其全部生活内容集中于一种纯粹的功能——认识自己和认识世界”。如果说“地下室人”带着19世纪内倾型人格的烙印,那么毕飞宇则通过观察当代,发现了新世纪的“地下室人”——傅睿。
傅睿是毕飞宇近来推出的新长篇《欢迎来到人间》中的主角,一位年轻有为的外科医生。阔别《推拿》《平原》《玉米》系列十五年后,毕飞宇在写“历史”之外,选择了日常经历中的“当代”。一百多年前,梁启超在《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夸饰小说的社会作用,从切近现实的角度来说,小说是能够做到抵达日常现象,还原生活本质的。毕飞宇写苏北乡村,也写现代都市,写乡村青年的淳朴与良善,也写城市里服务行业从事者的乐观与积极。在人物的跨度上,毕飞宇完成了一次转型,傅睿是他以往长篇小说中难见的城市精英形象,但又不具备精英该有的独当一面、圆通世故的能力,在自我和他者的设定中,傅睿从“我实际上是怎样一个人”模糊成“他应该是怎样一个人”。
故事以一件医疗事故为引子,泌尿外科是第一医院的王牌,却接连出现肾移植患者丧命的悲剧。第七位患者田菲的手术本来很成功,但还是因为感染身亡,主刀医生傅睿不仅因此碰上医闹,还遭遇了精神上的彻底崩盘,前数十年胜利的人生在此刻来到拐点。在小说的设定中,傅睿是父母、老师眼里的乖孩子、好学生,在同侪中一骑绝尘。然而就是这样一位近乎“高大全”的人物,在面对患者的死亡时却进入了难以穷尽的心灵迷宫,来自他者的设定被层层瓦解。
存在主义者萨特有一句名言,“存在先于本质”。傅睿的人生显然是走在相反的路上,他出生在高知家庭,父亲是第一医院的前任书记,母亲退休前是播音员,精英式教育决定他必须成为优秀的人。他会因为期末考卷上的标点错误而崩溃,会忙于作业而无视母亲受伤,这是一个冷漠、没有感情,只追求个人智力完美的“单向度的人”,与此相悖的是,他又是一个害怕考试的优等生,一个害怕死亡的外科医生。因为傅睿生来就已经被限定了人生轨迹,考试和手术意味着他人的凝视,但凡出现失误,他和人们心目中的那个“傅睿”就渐行渐远了。有一处细节,傅睿小学时成绩常居前茅,后来转来一个女生,成绩紧跟傅睿,一两分之差就会导致名次变化,傅睿正是因为这一两分,纠结于语文卷子的标点不放,这是典型的完美主义者。这种性格决定了他内心的强大,可以通过肯钻研的精神去瓦解人生路上的难题,另一面也注定了他的脆弱,某一天完美防线被击溃后,就只能迷失在先前自设的单一的上升之路中。
傅睿的人生很早就被决定了,他几乎丧失了生活的选择权。教育、择业、婚姻,这是基本的人生大事,但由于“本质论”,傅睿的人生轻易交由父母定夺。母亲在小学时就紧盯他的学习,父亲为他选择了医学方向,妻子敏鹿也是母亲相中的,傅睿在人际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几乎无力单独面对任何正常的人际交往,教学和实践中习得的一套职业术语成为他评断事物的标准。如此一来,他是在父母的愿望、自身的职业知识、众人的口耳相传中建构起来的人,是一个“被迫完美”却“失去完美”,最后因为“不完美”而精神崩溃的人。傅睿的人生是“本质先于存在”,父母决定了他是一个怎样的人,此后他就按照这样的方式去生活,就像一件达到质检标准的产品最终得以出厂,并且收获了广泛的赞誉。
和以往的作品相比,毕飞宇这次把笔触伸向了心理层面,通过稠密的心理自白,达成了对人物精神维度的探索。书中印刷的有两种字体,傅睿的心理幻想一律用楷体,自然进行的叙事节奏突然有波动,往往是傅睿逃逸现实,被心中幻境捕捉的时刻。比如他面对医院书记时,听着书记像父亲那样喋喋不休,幻想着拿起烟灰缸撒了书记一脸灰,并贸然冲出谈话室,实际这一幕并没发生,一切正常如旧,不过是傅睿心里幻想的一场战争。在想起患者田菲、护士小蔡时也有类似的心理游荡,毕飞宇在“心理现实主义”层面做出了成功的探索,傅睿心里所有的焦灼感都集中在绵密缠绕的文字中,作家凭借一流的语感,最大程度地让“言”能“尽意”。比如“他有了一个错觉,他不是经历了死亡与医患纠纷的医生,是战士。为了第一医院的荣誉,他顶着枪林弹雨,已经捐躯了。现在,第一医院终于迎来了他们的烈士。傅睿,作为烈士,正躺在雷书记的悼词里。雷书记在讴歌,傅睿在听。”毕飞宇在这里多用短句,整体语速较急促,形成一种压迫感和紧张氛围,作家使用语言技巧为人物的心理波澜造势,语言的另一头又连接着读者。
早先在《小说课》中,毕飞宇就表现出了扎实的文本细读功底,他了解读者的趣味,所以他是一位以高级读者身份写作的职业作家,熟悉怎么让读者通过“言”抵达人物的或作家的“意”,在阅读中享受咀嚼语言带来的爽脆感。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写大学生拉斯科尔尼夫斯基犯罪后的紧张心理时,采用了大段铺陈的手法,而毕飞宇则以轻巧的短句四两拨千斤,与此相对的是人物心理的沉重感。
“人的文学”是现代以降的一个中心话题,戴锦华教授评价毕飞宇刻画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人”,“现代人”不只是自然或生物意义上的人,更是丰富、多元、心理层面的作为精神实体的人。电影《大佛普拉斯》有句经典台词,“虽然现在已经是太空时代了,人类可以搭乘太空船到达月球,但却没办法看穿每个人心里的宇宙。”或许毕飞宇也是出于此种关切,才以“小说”的方式素描了当代人的精神实况,毋庸置疑,这是他从“历史”转向“现实”的一次诚意之作。
责任编辑:谢宛霏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 杨崇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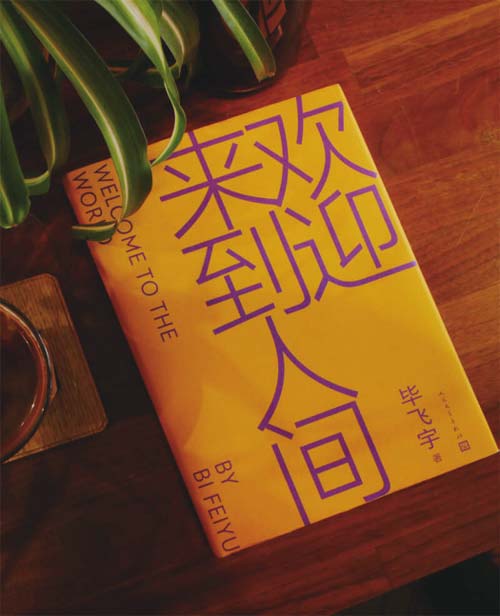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