屯上碉群
周春荣
来源:中国青年作家报
(2025年03月18日 15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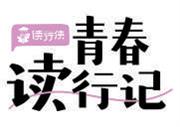
“没有我的时候,碉群在,我没有的时候,碉群仍在。”
龙年冬至那天,抵达贵州省纳雍县百兴镇垭口社区,第一次看到石材砌筑的谢家碉楼群落,我在心里默默地想起了这句话,心里有些“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一般的感伤。
百兴,旧称白泥屯。
屯,就是围起来的台地。我曾多次去过白泥屯,每一次,都被上苍赋予白泥屯的地形所震撼——那些泛称“断崖”的地表断层,从猴儿关开始呈现,沿着纳雍河及其支流的边缘,一路逶迤而去,崖上是平坦如砥的土地,崖下是奔流不息的大河。断崖连绵不绝,最后包抄到汪家坝附近,形成了一个“C”字形的天然屏障。
这个“C”字形断崖所圈起来的台地上,地势平坦,土壤厚实,筷子落地也会生根。因此,在农耕时代,就算不与外界互通有无,白泥屯人家也足以实现家给人足。基于白泥屯的“C”字形天然屏障,经久不息的民间谚语一直在传递着它的重要性:“好个白泥屯,四条路口进,来时耍大马,去时拄拐棍。”谚语中张扬出“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气势,道尽了白泥屯的地理优越。
我是经过“四条路口”中的猴儿关到达谢家碉群的。
首先把我引向碉群的,是来自百兴的新闻同事谢彦春与我在20年前的一次对话。那时,彦春说起谢家碉群的庞大与古老,神色中满是自豪,未见实物的我,只能附会碉群的形象与历史、峥嵘与没落。
最后把我引到碉群的,是百兴镇里的年轻干部胡宇——冬至那天,前往谢家碉群的路上,胡宇说,新中国成立前的白泥屯,有汪、胡、谢、王四大家族,一家有枪,一家有胆,一家有人,一家有钱,谢家就是有枪的人家,而胡宇的先辈,就是有胆的那一家。
四大家族同为屯上人家,因为都是一方水土上的一方人,他们尽管有时也有争端,但更多时候,他们却因为一个“屯”字的紧密关联而缔结成为一个整体,对来自外界的侵扰充满了一呼百应的同仇敌忾。
到达谢家碉群中的第一座碉楼前,胡宇联系了71岁的社区居民谢先华,让他把我们领进碉楼。
谢先华叫来的管理人员开了锁,打开了沉重木门,也打开了一个我曾经遐想过无数次的神秘世界。
碉楼共4层,每一层都有通往上一层的木梯,每一层都有瞭望孔、射击孔。瞭望孔开得比较大,孔中镶嵌了铜钱纹形状的镂空石材,射击孔的口子,外小里大,呈漏斗状,便于射手从里面转动枪口,调整射击覆盖范围。
碉楼的第四层上,中间修了木楼,木楼四周,是“回”字形的走廊,走廊的外围,是半腰高的石材栏杆。值哨的人可以沿着走廊全方位游动,以全方位的视野监视来自四面八方的一举一动。
顶上木楼的木材,已在漫漶风雨中渐渐腐蚀,而木楼脚下高达10多米的3层石碉,色泽依然还是当年的模样,那些一线一线的錾痕,仿佛还是刚刚开凿的样子。
站在顶楼的走廊上远望,只见包抄白泥屯的那些断崖延伸到了远处,像一条龙,倏然间就把龙头藏进了看不见的地方。如龙身一般的断崖,上面长满了灌木,它们在冬天依然葱绿,顽强地召唤着即将到来的春天;更远的远方,已经不属于百兴镇所属的纳雍县行政区划,而是属于织金、六枝的地盘,中间,隔了曾经浩浩汤汤的纳雍河、如今高峡平湖的黔中水库。
站在碉楼上,谢先华指着碉楼下一片开阔地说,这里曾经是织金前往白泥屯的陆上要冲。
谢家垭口处在白泥屯“四条路口”中的纳雍河岸一隅,20世纪初匪患猖獗的时候,谢家垭口是首当其冲受到外部骚扰的地带——来犯之匪只要渡过纳雍河,剩下的道路几乎都是一马平川。谢氏家族为了抵御匪患,以谢先华的曾祖父谢开文以及族人谢子南为头,众筹钱财,从1928年开始修筑谢家碉群,持续5年,建成碉楼4座。碉群的加持,不仅让谢氏家族的日子回到风平浪静,也让屯上的汪、胡、王三大家族免受来自外界的势力干扰。1949年后土匪的销声匿迹,碉群作为防御的功能被丢进历史垃圾堆,其中一座碉楼被拆了,石板被运到百兴街上铺筑百兴粮仓的院坝,原来的谢家大院也易主,成了王姓人家的地盘。而修筑谢家碉群的主人谢开文,则以一抷黄土的姿态,静卧在碉群旁边的荒草丛中……作为谢氏家族生生不息的见证,谢氏后裔依然保留着幸存的3座碉楼,让它们在朝晖夕阴中穿过一年又一年的春夏秋冬,与时间一样绵长地存在。
离开谢家碉群,我的心中仍然闪现着湮没在泥土之中的石条、矗立在路旁一隅的石碉。我想,如果时光停留在冷兵器时代,那些屯上人家,以及屯上受益于碉群保护的谢氏家族,应该是很有优越感的,因为易守难攻的地形足以阻挡一切的外来侵犯,也因为家给人足的无虞而用不着来自外界的帮衬,他们的生,与他们的活,都在一个封闭的系统里完成,并且完美。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每个人的一辈子,都在一个时间的闭区间内,有始,有终;而每一个无声的石材碉楼,应该都在一个时间的开区间里,与地老,与天荒。碉是人建的,建碉的人走了,碉还在,碉看着长大的那些人比如谢先华,也在以风一样的速度苍老,最终也会被绵长的时间覆盖。只有碉楼能够追赶时间,成为穿过朝晖夕阴的存在——碉楼,它就是一个无言的存在,穿过风,穿过雨,穿过时间。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责任编辑:宋宝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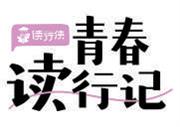
“没有我的时候,碉群在,我没有的时候,碉群仍在。”
龙年冬至那天,抵达贵州省纳雍县百兴镇垭口社区,第一次看到石材砌筑的谢家碉楼群落,我在心里默默地想起了这句话,心里有些“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一般的感伤。
百兴,旧称白泥屯。
屯,就是围起来的台地。我曾多次去过白泥屯,每一次,都被上苍赋予白泥屯的地形所震撼——那些泛称“断崖”的地表断层,从猴儿关开始呈现,沿着纳雍河及其支流的边缘,一路逶迤而去,崖上是平坦如砥的土地,崖下是奔流不息的大河。断崖连绵不绝,最后包抄到汪家坝附近,形成了一个“C”字形的天然屏障。
这个“C”字形断崖所圈起来的台地上,地势平坦,土壤厚实,筷子落地也会生根。因此,在农耕时代,就算不与外界互通有无,白泥屯人家也足以实现家给人足。基于白泥屯的“C”字形天然屏障,经久不息的民间谚语一直在传递着它的重要性:“好个白泥屯,四条路口进,来时耍大马,去时拄拐棍。”谚语中张扬出“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气势,道尽了白泥屯的地理优越。
我是经过“四条路口”中的猴儿关到达谢家碉群的。
首先把我引向碉群的,是来自百兴的新闻同事谢彦春与我在20年前的一次对话。那时,彦春说起谢家碉群的庞大与古老,神色中满是自豪,未见实物的我,只能附会碉群的形象与历史、峥嵘与没落。
最后把我引到碉群的,是百兴镇里的年轻干部胡宇——冬至那天,前往谢家碉群的路上,胡宇说,新中国成立前的白泥屯,有汪、胡、谢、王四大家族,一家有枪,一家有胆,一家有人,一家有钱,谢家就是有枪的人家,而胡宇的先辈,就是有胆的那一家。
四大家族同为屯上人家,因为都是一方水土上的一方人,他们尽管有时也有争端,但更多时候,他们却因为一个“屯”字的紧密关联而缔结成为一个整体,对来自外界的侵扰充满了一呼百应的同仇敌忾。
到达谢家碉群中的第一座碉楼前,胡宇联系了71岁的社区居民谢先华,让他把我们领进碉楼。
谢先华叫来的管理人员开了锁,打开了沉重木门,也打开了一个我曾经遐想过无数次的神秘世界。
碉楼共4层,每一层都有通往上一层的木梯,每一层都有瞭望孔、射击孔。瞭望孔开得比较大,孔中镶嵌了铜钱纹形状的镂空石材,射击孔的口子,外小里大,呈漏斗状,便于射手从里面转动枪口,调整射击覆盖范围。
碉楼的第四层上,中间修了木楼,木楼四周,是“回”字形的走廊,走廊的外围,是半腰高的石材栏杆。值哨的人可以沿着走廊全方位游动,以全方位的视野监视来自四面八方的一举一动。
顶上木楼的木材,已在漫漶风雨中渐渐腐蚀,而木楼脚下高达10多米的3层石碉,色泽依然还是当年的模样,那些一线一线的錾痕,仿佛还是刚刚开凿的样子。
站在顶楼的走廊上远望,只见包抄白泥屯的那些断崖延伸到了远处,像一条龙,倏然间就把龙头藏进了看不见的地方。如龙身一般的断崖,上面长满了灌木,它们在冬天依然葱绿,顽强地召唤着即将到来的春天;更远的远方,已经不属于百兴镇所属的纳雍县行政区划,而是属于织金、六枝的地盘,中间,隔了曾经浩浩汤汤的纳雍河、如今高峡平湖的黔中水库。
站在碉楼上,谢先华指着碉楼下一片开阔地说,这里曾经是织金前往白泥屯的陆上要冲。
谢家垭口处在白泥屯“四条路口”中的纳雍河岸一隅,20世纪初匪患猖獗的时候,谢家垭口是首当其冲受到外部骚扰的地带——来犯之匪只要渡过纳雍河,剩下的道路几乎都是一马平川。谢氏家族为了抵御匪患,以谢先华的曾祖父谢开文以及族人谢子南为头,众筹钱财,从1928年开始修筑谢家碉群,持续5年,建成碉楼4座。碉群的加持,不仅让谢氏家族的日子回到风平浪静,也让屯上的汪、胡、王三大家族免受来自外界的势力干扰。1949年后土匪的销声匿迹,碉群作为防御的功能被丢进历史垃圾堆,其中一座碉楼被拆了,石板被运到百兴街上铺筑百兴粮仓的院坝,原来的谢家大院也易主,成了王姓人家的地盘。而修筑谢家碉群的主人谢开文,则以一抷黄土的姿态,静卧在碉群旁边的荒草丛中……作为谢氏家族生生不息的见证,谢氏后裔依然保留着幸存的3座碉楼,让它们在朝晖夕阴中穿过一年又一年的春夏秋冬,与时间一样绵长地存在。
离开谢家碉群,我的心中仍然闪现着湮没在泥土之中的石条、矗立在路旁一隅的石碉。我想,如果时光停留在冷兵器时代,那些屯上人家,以及屯上受益于碉群保护的谢氏家族,应该是很有优越感的,因为易守难攻的地形足以阻挡一切的外来侵犯,也因为家给人足的无虞而用不着来自外界的帮衬,他们的生,与他们的活,都在一个封闭的系统里完成,并且完美。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每个人的一辈子,都在一个时间的闭区间内,有始,有终;而每一个无声的石材碉楼,应该都在一个时间的开区间里,与地老,与天荒。碉是人建的,建碉的人走了,碉还在,碉看着长大的那些人比如谢先华,也在以风一样的速度苍老,最终也会被绵长的时间覆盖。只有碉楼能够追赶时间,成为穿过朝晖夕阴的存在——碉楼,它就是一个无言的存在,穿过风,穿过雨,穿过时间。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责任编辑:宋宝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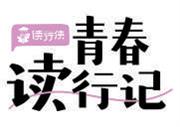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放大
放大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