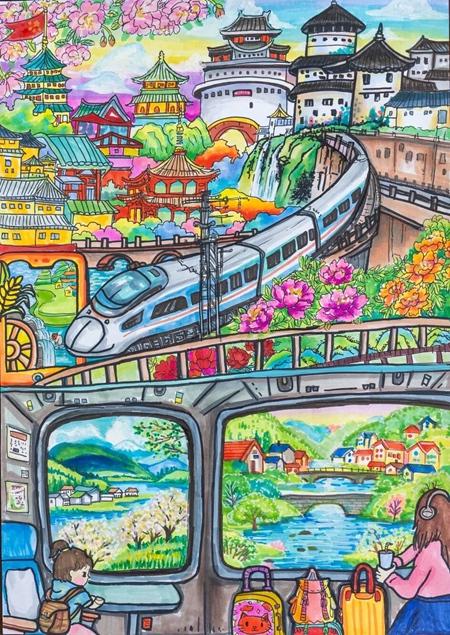
当钢铁巨龙穿梭于金秋大地,当列车载着团圆与期盼驶向远方,铁路早已不只是出行工具,更成为承载时代记忆、见证发展变迁的重要载体。
由中宣部文明创建局、中央网信办网络传播局、中国作协创联部、国家铁路集团党组宣传部联合主办的 “我的铁路风景”故事汇原创美文征集展示活动,日前正式启动。此次活动面向广大网友与旅客,征集散文、小说、诗歌、博文等原创文字作品,鼓励大家以笔为媒,讲述与铁路相关的鲜活故事 —— 无论是出行的温暖体验、旅途中的情感记忆,还是见证铁路发展的真切感悟,都欢迎投来。
投稿邮箱:zgqnzjb@cyd.cn
——————————
沿途的一切都与我有关(散文)
乔叶(北京作协副主席)
这些年也不知道坐过多少次高铁了。自打有了高铁,只要高铁能抵达的地方,只要路途不是太远,坐车的时间也不是太长,那高铁就是我出差的首选。多么好啊,高铁!能看风景是其一,主要是心里踏实,哪怕是打个盹儿,心里也踏实。窗外目之所及,就是坚实的大地,能不踏实吗?
粗算一下,东西南北各条线路的高铁,我都坐过。最常坐的是京广线,因老家在河南,现居在北京,每年都会在京豫之间往返几次甚或十几次。如果从这两地出发去别处的话,只要是往南北方向,那大概率就会乘坐京广线的高铁。记得某年6月初,我从郑州去深圳,原定的飞机因为频频的雷电天气一再延误,于是干脆退了机票,搭乘高铁,坐了7个多小时,把沿线的风景看了个够。
京沪高铁也是我熟悉的线路,自开通以来坐过好多次。最短的是从北京到天津,最长的就是坐了全程。途经站里,到过济南和泰安,还到过徐州、南京和昆山。无论长短途,我都贪恋窗外的风景,都觉得很有意思。
比如,看不够田野。只要出了城,就是田野。在城市中,常常觉得城市很大,可谓人海茫茫,楼海茫茫,车海也茫茫。出了城市就知道,还是田野更大。当然,到了山里又会觉得山很大,在海中又觉得海很大。可这大不同于那大,在心里,终归还是田野最大。这种执拗的感觉是因何而起?想来想去,也许是因为山海再大也都是自然的风景,这广袤的田野却是人为的。这一片片庄稼,这一片片庄稼包裹着的一个个村庄,意味的都是人,千千万万的人,以及他们的汗水和血泪。凡事一相关,就会觉得大。作为这些人中的一个,从这田野里感受到的大,是有温度的大,自然就是最大。
这田野上的田地,从没有闲的时候。一年四季,不是种这个,就是种那个。每个季节的庄稼都好看。冬春时的青翠麦苗,五黄六月的金色麦浪,夏末初秋亭亭玉立的玉米丛林,各有难以言喻的美。有一次,正值初夏时分,一览无余的平原上,麦子已经被收割过,只留下矮矮的麦茬。它的黄比土黄浅,比鹅黄硬,比杏黄暗,却原来,用它自己来形容自己才是最恰当。什么是麦黄色?这就是了。玉米呢,已经露出了绒毛般的翠绿——只有在这样的田野上,你才能领会到“苗头”这样用惯的词是多么美妙。
这真是勤勉的土地。再小的地块,哪怕是道路交叉口的一个锐角三角形,也会种着一两株南瓜或是几棵油菜。而它们呢,也是该开花就开花,该结果就结果。这也是“泼皮”的土地——“泼皮”这个词是我的豫北老家方言,翻译成普通话就是强韧,但我更喜欢用“泼皮”,因为它冒着一股鲜灵灵的水汽。这土地,总是让我心疼。可心疼的时候,又忍不住要嘲骂自己的矫情。
出了山东,进了江苏后,河流就明显多了起来。河流也让我看不够。事实上,河流在我这里没有很清晰的地域划分。河流是大地的血管,在漫长的历史烟云中,各个地方的人沿着这血管一路辗转迁徙,其间又纵横交织,关联和滋生出千丝万缕,自然就有很多融合杂缠。因此,很多地方虽然在行政分属上可以泾渭分明,但在文化意义上其实都是沾亲带故,语言、饮食、风土人情等元素怎么能彼此利落呢?着实是不好分那么清的。
行进中,大江大河亦如画卷一般徐徐展现。水已经不能用多来形容了。水在这里,就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土地。稻田也平整阔大起来,颇有点儿“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的歌词意蕴。船也多了。大大小小或不大不小的船,零零落落地行在或宽或窄的水上。是因为水的缘故吗?船总是显得缓慢从容,哪怕是那些装卸货物的船。远远地看着,就知道它们被压得很重,船舷沉沉地挨着水,总让我担心会进水。船们自然不会在意我这份徒劳的担心,它们无声地浮动着,一副心无挂碍的散淡模样。
我喜欢就这样默默地看着车窗外的一切,这沿途的一切。
很小的时候,第一次见到火车时,我就惊叹不已。铁轨,真是一种很神奇的存在。它明明不过是由一些干瘦的铁棍子组成的,却能让那么大的火车在上面轰隆隆地飞跑。每次火车跑过去之后,大地都会留下一阵轰隆隆的余震,以及一阵颤巍巍的余风。还有,它明明是窄窄的,窄得一步就能跨过去,却又是那么长,长得看不到尽头。
那时候,在我有限的想象里,铁轨就意味着远方,铁轨上呼啸而来又呼啸而去的火车就意味着远方。后来,我才知道,我错了。哪怕这火车跑得很快,哪怕这后来的高铁跑得更快。快,只是快而已,和远并没有关系。快,并不意味着远。你说,陀螺转起来的时候,快不快?但能说是远吗?同样的道理,火车跑得再快,也不过是在铁轨上。铁轨到哪儿,它就只能到哪儿。铁轨之外的地方,它到不了。所以,火车不等于远方。
所谓的远方,其实只有一个地方,那就是人心。
当然,最近的地方,也是人心。
因为这深广无边的人心,我爱看这沿途的一切。我知道,这沿途的一切都与我有关。村庄、河流、庄稼、树林、道路……一年年光阴,一代代人,一季季的春发夏长秋收冬藏,这一切意味的都是陌生且亲爱的人们的生活,他们既平凡又不平凡的生活。而我就身在其中,深在其中啊。
——————————
火车,火车(随笔)
李广宇
1
26岁那年,我参加青年志愿者活动,到贵州盘县当老师,虽然只有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可在那里的经历足够我用一生来回味。然后就是每年大连、贵州间的来来回回,如同候鸟,不是去那里怀念故旧,而是到那里偶遇我的学生们——最开始时,真的只是偶遇,刚刚辍学的学生们四处打工,能见到他们几乎全靠运气,后来他们开始陆续回到家乡,创业、成家、生育,慢慢变成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普通人。可在我的眼里,他们一点都不普通,我喊得出他们的名字,叫得出他们的外号,而且记得他们读书时的模样。被人记住大约是这世界上最幸福的事了,就如我,也被他们记得,当他们亲热地喊我一声“李老师”时,我的心都化了一般,甜。
当年的盘县,如今在地图上早已遍寻不见,取代它的是另一个名字。但我心里依旧固执地认为它就应该叫盘县,只有盘县才代表我曾经到过的那个地方。两河乡中学是我当年教书的地方,那里原来是个山清水秀的地方,我在很多文章里都记录过那里雨天的美丽与静谧、风夜的热闹与喧哗,当然也穷,学生们要翻山越岭来上学,中午吃不上饭,要硬扛着,坐在操场上晒太阳,让自己身体暖和起来……而这些如今只存在于我的回忆里了。
我一直觉得是火车改变了盘县的面貌,同时也改变了我的学生们的命运。当年偏僻的两河乡刚好就在如今高铁站的位置上,动迁征地让很多学生的家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时也让他们有机会进入到高铁的建设当中,在那场如火如荼的基建狂飙中获益。
2
冯熊每次来车站接我,都会开着不同的车,车子越来越豪华,他也越来越胖。一见面,我会拍着他的大肚子问,心宽体胖吗?他嘿嘿地笑,跟读书时一样害羞。他似乎只在我面前会害羞。
冯熊是最早参加高铁建设的学生之一。之前他做过很多临时工作,还被人骗过,从吉林某地逃出来后,他到大连来找我。那次我帮他买了回程车票,还给了他一点钱,这也成了十几年后,他每次见我都要说起的故事。
回贵州之后,冯熊在乡下种苞谷、养猪。我再去盘县时,忘记通知他,他听说我来,自己跑来找我,一身旧衣服,脸上带着诚惶诚恐的表情。那次他特意买了一箱饮料送我,然后没吃饭就要离开。
学生之间也存在着某种鄙视链,看得出其他同学都看不起他。我看得出来,只是不说,冯熊也如此。我独自送他去车站,他还是不知道说什么好的样子,最后才结结巴巴地说,李老师,下次来我家吃饭。
可惜我一直没能去他家做客。早先教他时,我去过他家家访,那是一个坐落在山坡上的小村子,风景极好,只是穷。冯熊穿着一件掉色的蓝布衣服,冲我跑来,喊着,李老师,走嘛,去我家嘛!唉,那情景早已刻进我的生命里。
十几年后,那个村子消失了,替代它的是巨大的高铁站。冯熊家拆迁后得到了大笔的补偿款,他用这些钱买下了卡车和挖掘机,而后承包了高铁站的建设项目,成了一个包工头。
上次见到他,他却已经从老板变成了盘县著名的“老赖”,每天无数人堵门讨债,逼得他不得不离开盘县去外地赚钱还债——冯熊一直没有放弃努力,他在外地开砂厂、接工程,他发誓要东山再起。有钱的时候,冯熊喊来所有能联系上的同学,KTV五颜六色的灯光下,他神态安然,话也不多。同学们在唱歌,他只是垂着眼睛听着,这时候大概是他最享受的时刻,他已经不是那个穿着旧衣、一身猪粪味道的乡下人。现在,同学们依旧看不起他,但这重要吗?冯熊一直孜孜以求地努力生活,仅仅这一点就让人感佩。人世艰难,只要不死,总还要坚强地活下去。冯熊在用他的人生告诉我这个道理。
3
马全还是那么腼腆,即便已经是一个孩子的父亲。我到盘县的那天晚上,他特意从昆明赶回来见我,但见面却不说话,只是笑,我问一句他答一句,跟读书的时候一样。他大概是我的学生里改变最小的一个了,身体跟当年一样壮实,表情跟当年一样木讷,待人却是真的好,贴心贴肺的那种,比女孩子还细腻。
在乡下教书的时候,我经常生病,学生们会想方设法收罗秘方给我治病,不知名的野果子、乌漆漆的树根,还有学生给我抓来黄鳝,让我放血泡酒,说是不但治病,而且长生不老,现在回想起来又好笑又感动。马全的父亲在乡下当兽医,他大概向父亲打听过,才给我带来了一根木头,我疑惑地问他是什么,他说这是“十大功劳”,煮水喝可以治你的病。我忍着笑,收下了,但没敢尝试。不料第二天一大早,马全就跑来宿舍敲门,问我好不好喝?我胡乱地点头,说好喝。
说实话,正是这“十大功劳”,让我对马全印象深刻。多年以后,我特意查过,还真有“十大功劳”这一味中药,独具清热解毒的功效,于我是对症的。
高铁的到来并没有改变马全家的状况。因为他家所在村子太偏僻,离高铁站很远。如果说有改变,就是他可以去高铁工地挖石子,还可以去更远的地方打工,比如昆明。
我问马全在昆明做什么?他说,跟着人家搞装修。我“哦”了一下,眼前的马全已经不是当年那个眼里充满阳光的大男孩。他的脸色黝黑,头发很长,手指粗糙,指甲缝里积满了黑泥,见我看他的手,他下意识地缩回去。我问,不想学医了?他摇摇头,迟疑了一下,才低声说,我说不好。
马全曾经多么痴迷成为一个医生。为了当医生,他自费去贵阳读培训班,回来却因为学历不够而不得不放弃资格证考试,后来他说他要学中医,可学中医又找不到肯收他为徒的老师……马全的想法曾经让我感觉他有些异想天开,可现在想想,只觉得惭愧——谁说咸鱼不能心怀翻身的梦想?
我本打算到昆明再找马全聊聊,谁知事情多,走的那天才想起他来,想想,还是下次再找他吧。找他,是有话要对他说。
梦想被岁月磨蚀了,可依旧会闪闪发光,它会在某个至暗时刻照亮我们的内心,让我们激情澎湃、热泪盈眶。一个人再平凡,一旦有了梦想,他就不再是普通的个体,这才是我们追求梦想的缘由。我一直想把这些告诉马全,还要告诉他,只要心怀梦想,就不要拒绝苦难、不要拒绝悲惨,人这辈子为了梦想而努力,才是最值得的活着的方式。
4
20多年过去,学生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有个人的选择,更有时代的痕迹,而其中高铁站带来的影响却是无比巨大的。高铁站让他们看到了山外的文明,并迅速被这种文明裹挟着进入城市化,让他们几乎毫不费力地成为城市居民。
这种变化在当下中国并不少见,或许只是因为这些人是我的学生,所以才会被我格外关注。我一直很喜欢高铁站背后的隐喻,就如同喜欢把我的学生们看成一列列远行才归的火车一样——高铁站是他们永远的家,即便他们走得再远,最终依旧要回到故土。
20多年里,我同他们当中的某些人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让我有机会目睹他们走过的路,与他们一起悲伤、一同欢喜。沧海桑田,两河乡中学的校舍可以翻新、旧宿舍可以拆掉,但我跟学生们的情谊却没有丝毫改变,当年我是他们的老师,现在我是他们的朋友。因为我的每次探望,他们才有了团聚的理由,才有了互相联络的机会,同时,也因为与他们的见面,让我时刻感受到成长的力量,感受到这个时代对个人的塑造与改变。
再平凡的生命也是一个精彩的小世界,再庸常的人生也有一丝照亮世界的光影,当我把一个人的生命放长到10年、20年,才看得清生命本底的亮色与暗影,这让我感到庆幸和愉悦。
这次离开盘县时,我特意选择到老火车站乘坐绿皮火车,不是怀旧,而只是想体会当年学生们离家外出时的惆怅与无奈。空荡荡的车厢里,光影腾挪,真的仿佛重回旧日,此刻,时光终于放慢了脚步……
——————————
那张旧时车票(散文)
娄国标
同学群里,有人晒出一张火车票。那是一张老式的硬板车票,出发站是家乡小镇,到达站是城里,车票时间是1995年6月的一天。
记忆的洪流,瞬间被这张旧车票激活。同学群难得热闹起来,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纷纷回忆起当年乘火年赶考的场景。
30年前的中考,考场设在城里。我们一帮乡村中学的孩子,在老师的带领下,乘火车去赶考。我和同学们大都是第一次坐火车,一路上既好奇,又忐忑。5毛钱的火车票,一趟绿皮火车,中间经停两个小站,带着我们来到城市,参加人生中第一场大考。
中考之后,同学们各奔东西,有人继续留在当地读高中,有人去了外地念中专技校,还有人则进入社会打拼生活。中考,就像是铁轨上的道岔,将大家的人生切换到不同的方向。
历经30年的岁月变迁,这张旧时车票,仿佛一条看不见的线,在过去与现在之间,牵引着我的思绪与情感。
行走在时光的记忆里,那个夏日的午后,沉默的站房,喧闹的站台,远道而来停靠的火车,鸣着震耳的汽笛,喘着沉重的粗气……这些,构成了脑海中不可磨灭的印记。我的旧时车票已经不知所终,但那趟火车带给我的感触,却时常叩击心灵。
对我来说,火车就像是一匹不知疲倦的野马,不知它来自哪里,但它在小镇车站停留片刻,带着我来到城里参加考试,又在一个深夜,载着我到省城读书,陪伴我开始漫长的远行之路。
一张火车票,打开我人生的一扇窗。机缘巧合,我参加工作成为铁路系统的一员,与火车结下了一辈子的缘分。
此后,我游走于铁路与火车之间,工作、出差、培训、探亲、上班下班、上车下车,见识了形形色色的旅客,也见证着铁路的发展、车票的变迁。很多时候,一张车票,就是一个故事,就是一段人生。
我曾弓着身子钻下地沟,仔细检修火车头走行部的每个部件,以一身汗水换取它的状态良好。
我曾在建设中的跨海大桥上,用镜头记录建设高铁的艰辛,为中国铁路迅猛发展高声放歌。
我曾踏上拥挤的春运列车,跟着游子们回乡的脚步,书写铁路人的坚守与付出,礼赞乡愁亲情与家国守望。
我曾在深夜的铁路线上,彻夜不眠参与钢轨与道岔的更换升级,为火车的安全正点运行,奉献如一颗道砟一般微薄的力量。
此时此刻,我无比怀想并感谢那张旧时车票,它上面印着日期、车次、座位号,也印着那一刻我的心情,印着由此而来的奋斗足迹。它不会被删除,不会仅存于云端,它就在我心灵的某个角落,安静地陪着岁月泛黄。
旧人、旧事、旧物,似乎成了我们一路上的不可或缺之物。不管有意无意,一些旧时痕迹,总会闪现出来,勾起回忆,激荡情绪。我想,或许每个人都有这么一张旧时车票,它浓缩着超越时空的相聚与思念,讲述着人间爱与悲欢的故事。
然而,在信息技术的加持下,车票的发展,让人猝不及防。在经历了几次升级换代之后,电子客票出现,纸质车票终将进入故纸堆。
时代推着我们往前,却总有一些东西,值得回头再看一眼。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在我们心中,都有一张车票,或通向远方,或走向归途。
——————————
追寻,从西宁到格尔木(组诗)
刘钊
脚底板还沾着去年的尘
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的风
在地图上吹了又吹,我总说“再等等”
等笔力练够,等空闲叠成厚纸
可青春的日子,像指缝漏的沙
越攥,越急着往远方跑
这次终于把背包扣紧
再踏上出发的路,从西宁向格尔木
把“寻”字,刻在鞋尖
坐火车往哈尔盖
车轮碾过星空的投影
昆仑卧在晨光里,露着青灰的背脊
青海湖随着车窗展开
像谁把天空,叠了一层水的软
风裹着湖的凉,撞在玻璃上
我没敢眨眼,怕错过某片云
落在山尖的模样,怕漏了
晨光漫过经幡的瞬间
窗外是一卷未合的书
每一根枕木,都写着西北的辽阔
下午到柯柯小镇
从前听人说柯柯,总带着秋天的黄
站在镇口,风裹着棱角峥嵘的冷
把枯枝吹得打颤,冻土下的草籽
还攥着去年的阳光
有一群人
在这里住了一年又一年
不知道还有多少个日夜
能把春的消息,从云里接过来
等那时,山野漫起新绿
连风,都该带着花的香了
夜宿乌兰
云在车顶跑,风裹着行程的急
从火车股道里下来,我盯着汽车颠簸
怕赶不上乌兰的夜,怕错过
一盏能接住疲惫的灯
终于把车停稳,路灯刚好点亮
把影子从地上扶起来,风也慢了
乌兰的夜色,像刚温好的茶
一口,就熨平了一路的急
初上大柴旦
风把荒坡的土卷起来
能看见枯草在里面晃,像没站稳的魂
寒冬把春的消息,藏得格外深
连阳光落下来,都带着冷色
目之所及,大地还没醒透
一群驻守的青年
他们的工装在风里飘,像荒坡上
刚开的花,红得格外亮
连手里的工具,都裹着暖
把荒芜,慢慢种成了希望
火车停留在格尔木
车轮的震颤才停
风里有了戈壁的味道
混着盐湖的咸
车门口,落日斜斜扫过铁轨
把锈迹照得发亮
乘务员匆忙的脚步声把思绪拉回
昆仑的雪顶还在远处悬着
把内心的静,衬得格外清透
从格尔木返程
去时快要落下的月亮,留在背包上
返程时,星星已落满车顶
火车的车轮没停
从辽阔的湖,到狂风中的山
镜头里存的
不只是风光,还有那群人
现在若有人问起青藏铁路的模样
我不必说太多
只把镜头打开
风会替我,把那些日子
慢慢讲
见习编辑:赵小萱
责任编辑:周伟

 上一版
上一版





 放大
放大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