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深处的老城(散文)
范必信
来源:中国青年作家报
(2025年12月30日 14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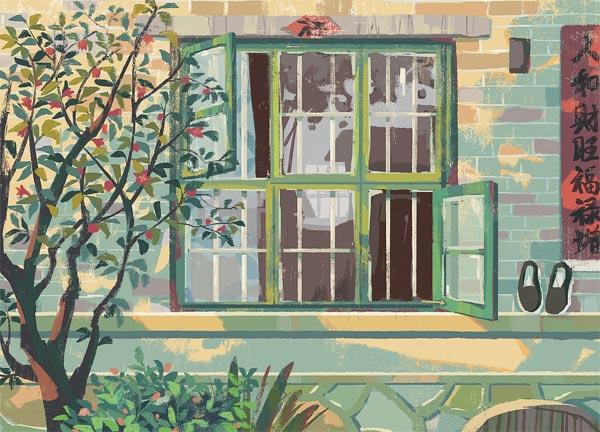
随父母亲回了一趟老城,记忆被一页页翻开。我在那陈旧的时光中出生、成长,蓦一回首,已经人城两殊。多年前,在“设市撤县”的惊雷中,老城卸下“城”的冠冕,露出了“镇”的真容。在流光侧影里,家人陆续迁往新城,至此,老城于我,忆比见多。
闷热夏季里骤然而至的一场太阳雨,雨点急促如杂乱的音符,噼啪砸在教室窗上,引得众人一片哗然后又归复朗朗晴空,只弯出一道彩虹横跨山头。那是老城难得的澄净时刻,应了那句“铅华洗净,珠玑不御”。记忆中,这个嵌在山坳里的小城,像极了一位穷其一生追求美貌却又不得章法的女子,胭脂水粉尽数堆砌在脸上,举手投足间,却掩不住山野本色。
那时候的我还不懂得什么叫作“煤矿大县”,只觉得老城哪里都像是覆了一层刷不净的煤灰,要么灰扑扑,要么黑乎乎。依稀记得,有一位母亲带着几个孩子专门给别人家“踩煤”。最小的一个,她用洗得败了色的“背篼”背在背上,最大的孩子估摸也只有七八岁。卖煤的用马车拉来后卸在东家的院子门口,这位母亲又用板子车拉来一车黄土掺在煤里,加上水以后用铁锹和匀。她把裤脚卷得老高,赤着脚反复地踩,直到那一大堆煤土混合物变得黏稠,她就用一对簸箕把它们挑到东家指定的位置堆好,再挑来水把踩煤的路面清洗干净。有时候,她的几个孩子也学着她的模样,赤着小脚丫踩煤。这样踩出来的煤,烧出来的烟极其呛人,但燃烧时间很长。
我家就储藏了一整个地下室的煤,堆好的煤在干燥后变得硬邦邦的,一到冬天,父亲便拿着簸箕和铁锤进地下室敲下煤块生火。
城里那条算不上宽阔的护城河浑浊不堪,由两条穿城而过的小河汇集而成,在那河道交汇处常常是一黑一黄,让人摇头叹息:大煞风景。可父亲那一辈的人却同我说,这条河曾是这个小城的母亲河。他们幼年时,放学便要提着两只水桶到街口接水,那个被铁盒子锁起来的水龙头还有专人看管,接两桶水就要花一分钱水票。接回去的水金贵得很,只用于吃喝,除此之外的用水,一些取自山半腰的水井,但更多的是就近取自那条护城河。他们不仅在河中取水洗衣、洗澡,还捞鱼捉虾,早早地便学会了游泳这项技能。这条河不知从什么时候变得与他们儿时记忆不相吻合的,只剩那沿河一路的垂柳,在风吹雨打间各自生出了不同的姿态,以绰约之影安静凝视着那默然无言的河。而后,随着河道治理工程的开展,老城的河水终于恢复了清可见底的模样,但路边的垂柳,却不得不又重新栽种了一次,年轻的柳树疏疏落落,垂下那几枝柳条甚至遮不住河道,不复以往那般。
比之河道旁那落寞的垂柳,生长在主干道两旁的法国梧桐,倒是向来都是热闹的。它们热衷于在春季播散细小绒毛,粗壮的根系又不愿向下深扎,沉迷于撬动人行道上的那几块地砖,听着行人一个接一个地打喷嚏,看着地砖下的污水一次又一次溅脏行人的裤管,它们又更加乐呵地尽情舒展身姿,全然顾不得那些枝叶是否会剐蹭到路过的大巴车。我曾经羡慕过书中那些大城市独有的行道树,上海的云南杉松,应当是满怀闲情逸致的吧,安徽某个县城的望春花树,大抵是优雅而高洁的吧。而老城的这些法国梧桐,似是过于喧嚷了,可转念一想,就这眼前老城的拥堵杂乱,又与它们十分合衬了。坍圮了一半的老城墙,朱漆剥落的文庙,苍凉荒寂的公馆,被烟火燎得漆黑的城门洞……它们的沉闷和颓然,以秋为信,以梧桐的黄叶为笺,也算写就了这唯一的老城。
老城的周末是“赶场天”,本就不宽敞的街头巷尾都支满了棚伞和摊位,锅碗瓢盆、衣帽鞋裤、红绸白布、香蜡纸钱,简直一应俱全。一些老乡更是拿着塑料袋和麻皮袋往人行道上一铺,拣出背篓里的时令果蔬就地开卖。新鲜的小红梨和浑身带刺的刺梨,酸中带涩,把山果历经风雨洗礼的风味一并送入买家口中。“赶场天”,老城的交通比之平日里更为水泄不通,几近瘫痪。行人摩肩擦踵,老乡身上的旱烟味、泥土味,接连不断地往鼻子里冲,混杂着街头传来一股股茶油鸭的香气,和巷尾又飘来的阵阵鸡蛋糕的甜腻,行走其中,倒是真能体会一次字面意义上的“五味杂陈”。
老城的时间极好打发,那些平日里的所见所闻最终只能归为令人倦怠、平淡无奇,而那个空旷的、被黄沙铺满的“校(jiào)场坝”倒勉强算得上有点意思。“校场坝”用现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一个露天运动场。我也曾思考过很多次有关“校场坝”这个称呼的由来,在本地话中,“场坝”应当是指历史上用于集市交易的空旷场地或市场,前面加上“校”字,倒是多出了“沙场秋点兵”的意味了。
偌大的空地,被半人高的铁栅栏围着,临街傍河,一侧是小城最繁华的主街,故而也有几个小型的用以招揽客人的秋千、蹦床等;另一侧隔着河遥望山上的烈士陵园,而那山脚下则是骇人的殡仪馆。这个“校场坝”的位置由此显得非常奇特,对于年幼的我而言,既是唯一可去的游乐场所,又是联想鬼怪志异故事的好去处。这“校场坝”作为老城人民茶余饭后散步的最佳去处,用它场内为数不多的草坪承接了太多孩童的欢乐,我也是其中之一。我们在草地里找到看上去最为坚韧的草,双方拉扯至一方断裂,断者输,输家便要请一顿两角钱的泡萝卜或者五角钱的棉花糖,然后便嬉笑打闹至天色渐黑。
有时候我们也会在那里放风筝,一把白胡须的老太爷用竹蔑扎出一个又一个形态迥异的风筝骨架,刷上糨糊,裱上五颜六色的纸,最后一笔一笔地画出鸟兽、鱼虫等等。最令人羡慕的当然是那长长一串“蜈蚣风筝”,飞上天去好不威风。“校场坝”里常常有各式各样的活动,我们小孩子在那里一待就是一整天。拾捡“刮刮乐”的卡片做成各类玩具,跟着打腰鼓、扭秧歌的文艺队有样学样,撵着各个舞龙队伍蹭个乐呵……然而好景不长,我钟爱的这片乐园终被挖土机和吊塔所占据,原址上立起了一座商业广场。父亲对此的评价是:“带洋不土的。”
我从未察觉到老城有拿得出手的美景,仅有一个叫作“碧云洞”的地方略有人气,当地人称“水洞”。读了高中我才从地理书里知道,不过是个喀斯特溶洞而已。小是小了点,但有幸在徐霞客笔下得以记录而成为小城的“知名景点”。每年农历正月二十三,便有“游水洞”的传统民俗活动,又称“游百病”,寓意通过出游“水洞”祈求健康平安。
初去时,我不过六七岁。未近山门,便觉凉意扑面,哗哗水声已让脚底似是浸了寒水。山门那威武的石狮子在老城属实罕见,哪怕是进了山门,我还一步三回头地念念不忘。我头一次如此真实地感到自身的渺小。站在山脚下抬头仰望那近在咫尺的山,那座理应只是匍匐于老城南边的小山,众人口中的“小土包”,竟是怪石嶙峋、崖刃百丈,这让我首次对山之巍峨有了模糊的认知。再往后的这些年里,我见过很多的山,灵秀的、峻险的、雄壮的、高耸的,却怎样也磨灭不了我第一次见这座山时的惊诧。那是浑然没有束缚的自由感,仿佛自己只是那山中的一棵树、一朵花,甚至一阵微风。这样的感触,与我爬上老城东边的文笔山后,被那古朴而又玄妙的文笔塔摄了魂般如出一辙。许多年里,我仍在梦里一遍又一遍地望见那片铺天盖地的粉色黛子草,拥簇着那透着青灰色的文笔塔,形似巨笔矗立,塔顶的缺损处似是随时都能迸发出耀眼的光来。在“水洞”,我怀揣着那一份小小的悸动,行过水流湍急的木板桥,探寻了可能有娃娃鱼的出水洞,穿过了深邃又阴森的燕子洞,步曲径、爬天梯、过栈道,将“奇妙”二字悄然记于心头却又不自知。
老城还是太老了。当街便有一排排低矮的瓦房,饱经日晒雨淋、烟熏火烤的木制框架早已是一派摇摇欲坠的架势,沿着房檐牵出的电线四处无力地耷拉着,被绝缘胶带缠绕的地方像是隆起的丑陋瘤子。而那些古迹,自然更是残缺不全、疮痍满目,目之所及之处全然是岁月无情的痕迹,有何美感可言?可老一辈的人还在娓娓而谈:“我们这里可了不得啊,明清两代总共出了17名进士,171个举人嘞!晓得不,这叫文运昌盛,要有文化底子才养得出这么多文化人的嘛!”我是全然听不进去的。
在老城居住的那许多年间,“索然无趣”这几个字也不知是何时何地、由哪一根筋里执拗地冒了出来,且再也压不住。兴许是因为在老城没能吃上一次正牌的炸鸡“全家桶”,又或者是因为这里没有公交车……就算把整个小城翻个底朝天,卖宣纸的也就那独一号的店。总而言之,日复一日,我渐渐对老城周遭的一切视若无睹,就连春日成片的樱桃花,夏季满池的粉荷,也都变得毫无意义。我开始向往所谓的高楼林立和夜间霓虹,幻想着大都市那齐整的街道和叮当作响的地铁闸机。老城啊,它被山包围着,一圈又一圈的山,你好不容易登上一个山顶,却发现视线所及之处,仍然是山。那一座座蜿蜒曲折的山啊,困住了这座城,似乎也困住了我。于是,我决心要挣脱老城,要走出那一座座山去。
我如今真的身处老城之外了,日日看着50米开阔的街道车水马龙,人行道上站着一棵棵笔直的银杏,公园的野鸭惬意地划开湖面,夜间的灯火流光溢彩……可这新城啊,喧嚣的时候过于喧嚣,有响不停的鸣笛声、散不去的划拳声,寂寞的时候又太寂寞,邻里间的互不相识、老一辈的无所事事。新城里什么都好,却又让人时感空虚,以至于瑰丽的晚霞都要透过车头的后视镜去凝视。
我总在年头年尾蓦然想起我的老城来。正月里,鞭炮声在老城里此起彼伏,每条街都会请出代表街道门面的“龙头”,9条街,便有9条不同颜色、不同长度的“龙”被舞动。孩子们在除夕夜祈求夜里的雪再下得大些,第二天便能早早地换上一身新装去雪地里踩个咯吱响,还能搂着在楼顶和桥墩上堆的干净的积雪来堆雪人、打雪仗。他们揣着压岁钱,路过的每一个小摊都承载着他们的快乐,啃着酸溜溜的泡梨,又咬一口甜津津的糖葫芦,一路追着舞龙舞狮的队伍穿过大半个老城,给一些商铺老板送上点吉利话,讨一个小小的红包或者几颗满含新年祝福的糖果。
这次回到老城,站在窗前,我猛然发现,老家的窗户是没有防护栏的,一整扇窗,推开,入眼的便是整个世界。儿时,我常常坐在窗边观望变幻莫测的云,澎湃的火烧云,低沉的积雨云……但在新城的那个“家”里,银光凌冽的防护栏甚至把天空都切割开来。我又想起了父亲在老家阳台种下的花草树木,一丛丛兰、一枝枝竹,攀岩的爬山虎,倒挂的蔷薇花,娇嫩的石榴花,还有花期很长的三角梅……那些个数不清的傍晚,我坐在阳台上,借着夕阳的余晖,观摩远方山的轮廓剪影,层层叠叠、连绵不绝,那一个个山头又都似我的老朋友一般,在茫茫夜色里予以我饱含深情的对望。
回新城的路,依旧是那一条。车子绕过一个又一个熟悉的山头,将老城远远地甩在身后,直至它在夜幕中凝成一片微弱的萤火。原来,困住我的从来不是那些山,而我的老城也并不老。当我终于走出群山,才发现我曾奋力挣脱的,是生命中最扎实的根底;我曾嗤之以鼻的,是岁月里最明媚的烟火。车窗外的世界飞速后退,我兜兜转转,似乎真的离开了那片山,但我知道,我永远也离不开,我的老城。
见习编辑:赵小萱
责任编辑:周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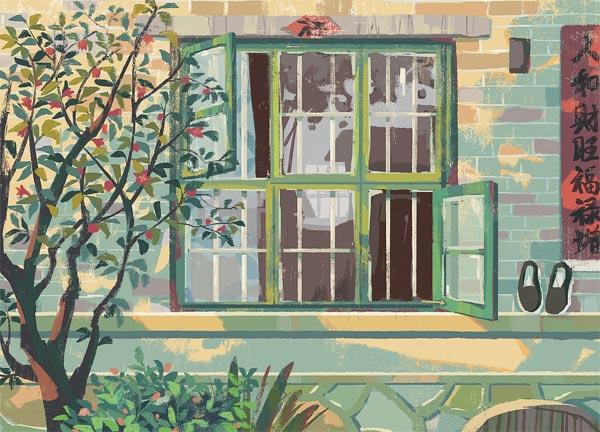
随父母亲回了一趟老城,记忆被一页页翻开。我在那陈旧的时光中出生、成长,蓦一回首,已经人城两殊。多年前,在“设市撤县”的惊雷中,老城卸下“城”的冠冕,露出了“镇”的真容。在流光侧影里,家人陆续迁往新城,至此,老城于我,忆比见多。
闷热夏季里骤然而至的一场太阳雨,雨点急促如杂乱的音符,噼啪砸在教室窗上,引得众人一片哗然后又归复朗朗晴空,只弯出一道彩虹横跨山头。那是老城难得的澄净时刻,应了那句“铅华洗净,珠玑不御”。记忆中,这个嵌在山坳里的小城,像极了一位穷其一生追求美貌却又不得章法的女子,胭脂水粉尽数堆砌在脸上,举手投足间,却掩不住山野本色。
那时候的我还不懂得什么叫作“煤矿大县”,只觉得老城哪里都像是覆了一层刷不净的煤灰,要么灰扑扑,要么黑乎乎。依稀记得,有一位母亲带着几个孩子专门给别人家“踩煤”。最小的一个,她用洗得败了色的“背篼”背在背上,最大的孩子估摸也只有七八岁。卖煤的用马车拉来后卸在东家的院子门口,这位母亲又用板子车拉来一车黄土掺在煤里,加上水以后用铁锹和匀。她把裤脚卷得老高,赤着脚反复地踩,直到那一大堆煤土混合物变得黏稠,她就用一对簸箕把它们挑到东家指定的位置堆好,再挑来水把踩煤的路面清洗干净。有时候,她的几个孩子也学着她的模样,赤着小脚丫踩煤。这样踩出来的煤,烧出来的烟极其呛人,但燃烧时间很长。
我家就储藏了一整个地下室的煤,堆好的煤在干燥后变得硬邦邦的,一到冬天,父亲便拿着簸箕和铁锤进地下室敲下煤块生火。
城里那条算不上宽阔的护城河浑浊不堪,由两条穿城而过的小河汇集而成,在那河道交汇处常常是一黑一黄,让人摇头叹息:大煞风景。可父亲那一辈的人却同我说,这条河曾是这个小城的母亲河。他们幼年时,放学便要提着两只水桶到街口接水,那个被铁盒子锁起来的水龙头还有专人看管,接两桶水就要花一分钱水票。接回去的水金贵得很,只用于吃喝,除此之外的用水,一些取自山半腰的水井,但更多的是就近取自那条护城河。他们不仅在河中取水洗衣、洗澡,还捞鱼捉虾,早早地便学会了游泳这项技能。这条河不知从什么时候变得与他们儿时记忆不相吻合的,只剩那沿河一路的垂柳,在风吹雨打间各自生出了不同的姿态,以绰约之影安静凝视着那默然无言的河。而后,随着河道治理工程的开展,老城的河水终于恢复了清可见底的模样,但路边的垂柳,却不得不又重新栽种了一次,年轻的柳树疏疏落落,垂下那几枝柳条甚至遮不住河道,不复以往那般。
比之河道旁那落寞的垂柳,生长在主干道两旁的法国梧桐,倒是向来都是热闹的。它们热衷于在春季播散细小绒毛,粗壮的根系又不愿向下深扎,沉迷于撬动人行道上的那几块地砖,听着行人一个接一个地打喷嚏,看着地砖下的污水一次又一次溅脏行人的裤管,它们又更加乐呵地尽情舒展身姿,全然顾不得那些枝叶是否会剐蹭到路过的大巴车。我曾经羡慕过书中那些大城市独有的行道树,上海的云南杉松,应当是满怀闲情逸致的吧,安徽某个县城的望春花树,大抵是优雅而高洁的吧。而老城的这些法国梧桐,似是过于喧嚷了,可转念一想,就这眼前老城的拥堵杂乱,又与它们十分合衬了。坍圮了一半的老城墙,朱漆剥落的文庙,苍凉荒寂的公馆,被烟火燎得漆黑的城门洞……它们的沉闷和颓然,以秋为信,以梧桐的黄叶为笺,也算写就了这唯一的老城。
老城的周末是“赶场天”,本就不宽敞的街头巷尾都支满了棚伞和摊位,锅碗瓢盆、衣帽鞋裤、红绸白布、香蜡纸钱,简直一应俱全。一些老乡更是拿着塑料袋和麻皮袋往人行道上一铺,拣出背篓里的时令果蔬就地开卖。新鲜的小红梨和浑身带刺的刺梨,酸中带涩,把山果历经风雨洗礼的风味一并送入买家口中。“赶场天”,老城的交通比之平日里更为水泄不通,几近瘫痪。行人摩肩擦踵,老乡身上的旱烟味、泥土味,接连不断地往鼻子里冲,混杂着街头传来一股股茶油鸭的香气,和巷尾又飘来的阵阵鸡蛋糕的甜腻,行走其中,倒是真能体会一次字面意义上的“五味杂陈”。
老城的时间极好打发,那些平日里的所见所闻最终只能归为令人倦怠、平淡无奇,而那个空旷的、被黄沙铺满的“校(jiào)场坝”倒勉强算得上有点意思。“校场坝”用现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一个露天运动场。我也曾思考过很多次有关“校场坝”这个称呼的由来,在本地话中,“场坝”应当是指历史上用于集市交易的空旷场地或市场,前面加上“校”字,倒是多出了“沙场秋点兵”的意味了。
偌大的空地,被半人高的铁栅栏围着,临街傍河,一侧是小城最繁华的主街,故而也有几个小型的用以招揽客人的秋千、蹦床等;另一侧隔着河遥望山上的烈士陵园,而那山脚下则是骇人的殡仪馆。这个“校场坝”的位置由此显得非常奇特,对于年幼的我而言,既是唯一可去的游乐场所,又是联想鬼怪志异故事的好去处。这“校场坝”作为老城人民茶余饭后散步的最佳去处,用它场内为数不多的草坪承接了太多孩童的欢乐,我也是其中之一。我们在草地里找到看上去最为坚韧的草,双方拉扯至一方断裂,断者输,输家便要请一顿两角钱的泡萝卜或者五角钱的棉花糖,然后便嬉笑打闹至天色渐黑。
有时候我们也会在那里放风筝,一把白胡须的老太爷用竹蔑扎出一个又一个形态迥异的风筝骨架,刷上糨糊,裱上五颜六色的纸,最后一笔一笔地画出鸟兽、鱼虫等等。最令人羡慕的当然是那长长一串“蜈蚣风筝”,飞上天去好不威风。“校场坝”里常常有各式各样的活动,我们小孩子在那里一待就是一整天。拾捡“刮刮乐”的卡片做成各类玩具,跟着打腰鼓、扭秧歌的文艺队有样学样,撵着各个舞龙队伍蹭个乐呵……然而好景不长,我钟爱的这片乐园终被挖土机和吊塔所占据,原址上立起了一座商业广场。父亲对此的评价是:“带洋不土的。”
我从未察觉到老城有拿得出手的美景,仅有一个叫作“碧云洞”的地方略有人气,当地人称“水洞”。读了高中我才从地理书里知道,不过是个喀斯特溶洞而已。小是小了点,但有幸在徐霞客笔下得以记录而成为小城的“知名景点”。每年农历正月二十三,便有“游水洞”的传统民俗活动,又称“游百病”,寓意通过出游“水洞”祈求健康平安。
初去时,我不过六七岁。未近山门,便觉凉意扑面,哗哗水声已让脚底似是浸了寒水。山门那威武的石狮子在老城属实罕见,哪怕是进了山门,我还一步三回头地念念不忘。我头一次如此真实地感到自身的渺小。站在山脚下抬头仰望那近在咫尺的山,那座理应只是匍匐于老城南边的小山,众人口中的“小土包”,竟是怪石嶙峋、崖刃百丈,这让我首次对山之巍峨有了模糊的认知。再往后的这些年里,我见过很多的山,灵秀的、峻险的、雄壮的、高耸的,却怎样也磨灭不了我第一次见这座山时的惊诧。那是浑然没有束缚的自由感,仿佛自己只是那山中的一棵树、一朵花,甚至一阵微风。这样的感触,与我爬上老城东边的文笔山后,被那古朴而又玄妙的文笔塔摄了魂般如出一辙。许多年里,我仍在梦里一遍又一遍地望见那片铺天盖地的粉色黛子草,拥簇着那透着青灰色的文笔塔,形似巨笔矗立,塔顶的缺损处似是随时都能迸发出耀眼的光来。在“水洞”,我怀揣着那一份小小的悸动,行过水流湍急的木板桥,探寻了可能有娃娃鱼的出水洞,穿过了深邃又阴森的燕子洞,步曲径、爬天梯、过栈道,将“奇妙”二字悄然记于心头却又不自知。
老城还是太老了。当街便有一排排低矮的瓦房,饱经日晒雨淋、烟熏火烤的木制框架早已是一派摇摇欲坠的架势,沿着房檐牵出的电线四处无力地耷拉着,被绝缘胶带缠绕的地方像是隆起的丑陋瘤子。而那些古迹,自然更是残缺不全、疮痍满目,目之所及之处全然是岁月无情的痕迹,有何美感可言?可老一辈的人还在娓娓而谈:“我们这里可了不得啊,明清两代总共出了17名进士,171个举人嘞!晓得不,这叫文运昌盛,要有文化底子才养得出这么多文化人的嘛!”我是全然听不进去的。
在老城居住的那许多年间,“索然无趣”这几个字也不知是何时何地、由哪一根筋里执拗地冒了出来,且再也压不住。兴许是因为在老城没能吃上一次正牌的炸鸡“全家桶”,又或者是因为这里没有公交车……就算把整个小城翻个底朝天,卖宣纸的也就那独一号的店。总而言之,日复一日,我渐渐对老城周遭的一切视若无睹,就连春日成片的樱桃花,夏季满池的粉荷,也都变得毫无意义。我开始向往所谓的高楼林立和夜间霓虹,幻想着大都市那齐整的街道和叮当作响的地铁闸机。老城啊,它被山包围着,一圈又一圈的山,你好不容易登上一个山顶,却发现视线所及之处,仍然是山。那一座座蜿蜒曲折的山啊,困住了这座城,似乎也困住了我。于是,我决心要挣脱老城,要走出那一座座山去。
我如今真的身处老城之外了,日日看着50米开阔的街道车水马龙,人行道上站着一棵棵笔直的银杏,公园的野鸭惬意地划开湖面,夜间的灯火流光溢彩……可这新城啊,喧嚣的时候过于喧嚣,有响不停的鸣笛声、散不去的划拳声,寂寞的时候又太寂寞,邻里间的互不相识、老一辈的无所事事。新城里什么都好,却又让人时感空虚,以至于瑰丽的晚霞都要透过车头的后视镜去凝视。
我总在年头年尾蓦然想起我的老城来。正月里,鞭炮声在老城里此起彼伏,每条街都会请出代表街道门面的“龙头”,9条街,便有9条不同颜色、不同长度的“龙”被舞动。孩子们在除夕夜祈求夜里的雪再下得大些,第二天便能早早地换上一身新装去雪地里踩个咯吱响,还能搂着在楼顶和桥墩上堆的干净的积雪来堆雪人、打雪仗。他们揣着压岁钱,路过的每一个小摊都承载着他们的快乐,啃着酸溜溜的泡梨,又咬一口甜津津的糖葫芦,一路追着舞龙舞狮的队伍穿过大半个老城,给一些商铺老板送上点吉利话,讨一个小小的红包或者几颗满含新年祝福的糖果。
这次回到老城,站在窗前,我猛然发现,老家的窗户是没有防护栏的,一整扇窗,推开,入眼的便是整个世界。儿时,我常常坐在窗边观望变幻莫测的云,澎湃的火烧云,低沉的积雨云……但在新城的那个“家”里,银光凌冽的防护栏甚至把天空都切割开来。我又想起了父亲在老家阳台种下的花草树木,一丛丛兰、一枝枝竹,攀岩的爬山虎,倒挂的蔷薇花,娇嫩的石榴花,还有花期很长的三角梅……那些个数不清的傍晚,我坐在阳台上,借着夕阳的余晖,观摩远方山的轮廓剪影,层层叠叠、连绵不绝,那一个个山头又都似我的老朋友一般,在茫茫夜色里予以我饱含深情的对望。
回新城的路,依旧是那一条。车子绕过一个又一个熟悉的山头,将老城远远地甩在身后,直至它在夜幕中凝成一片微弱的萤火。原来,困住我的从来不是那些山,而我的老城也并不老。当我终于走出群山,才发现我曾奋力挣脱的,是生命中最扎实的根底;我曾嗤之以鼻的,是岁月里最明媚的烟火。车窗外的世界飞速后退,我兜兜转转,似乎真的离开了那片山,但我知道,我永远也离不开,我的老城。
见习编辑:赵小萱
责任编辑:周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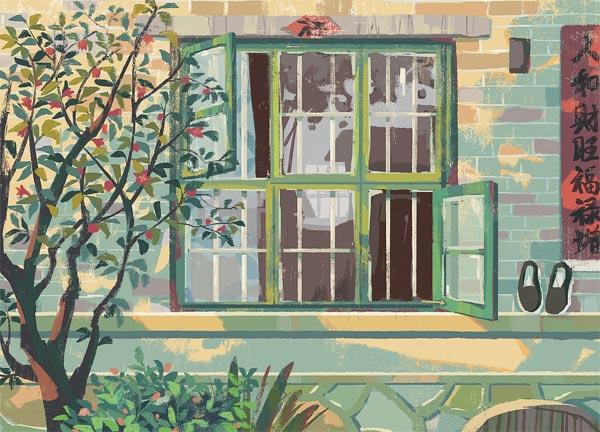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放大
放大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