昏黄的月光趁着夜色写下了7首诗,他寂寞,因为没有人读懂他。他把这7首诗送往另一个时空,让它们住进7个诗人的灵魂里,从此,诗歌便有了它们的名字。
诗人敬重光明,也祭奠黑暗。他们敬畏普罗米修斯,不是因为他敢于盗火,而是选择把火种传给最智慧的人类,从此,人们便有了温暖与光明。可爱的诗人们也想做一个艺术的“窃火者”,用火石创造第一个字和最后一句诗。
南方的诗,沉沉地睡着;北方的诗,却警醒着。它们打开尘封的百年记忆,逃出信函。
简约的文言收到通俗白话的长函后,偶然碰见个诗人。这位诗人单身匹马而往,正练习白话文。“你不能做我的诗,正如我不能做你的梦。”这诗人便是胡适,他把新白话诗藏进第一个信函里,把它叫做《梦与诗》。在这个信函里,诗歌第一次告别“文言诗国”,以生动的姿态走向白话的国度。至此,芬芳、华美、欢乐与寂寥、衰败、哀伤一同出现在信笺上,它们划过长长的笔墨,在一个忍静的文明里开出一朵涅槃之花,掷地有声。坚守着超越物质环境的潜能,一个个静默的灵魂共同迈入新的语言国度。
第二个信函飘啊飘,折成一只小小的纸船。诗人冰心小心地捡起每一只被时光隧道的跫音抖落的白船儿,让它们游入大海,或躲进梦乡。“万水千山,求它载着她的爱和悲哀归去。”繁星默默祈祷,它们越过邃蓝的天际飞向诗人,化作诗人笔下沉默中的微光。那些遗失的和遗失者在一起,在随波逐流的诗页中找寻记忆的碎片。诗人说,盛夏带走了我的温柔,也带走了你,所以我一直在等待你。信函说,最后一片绿叶的掉落,是我在捕捉你的声音,我比冬天先到来了,因为,这是我最后一次营救你。
11月的阳光,谙而不语。第3个信函静静地躺在一片陌生的森林中。他看到诗人徐玉诺“轻轻地捧起那些奇怪的小诗,慢慢走入林去”。杂乱的乐符与神秘的诗丝交织着,生出美妙的乐曲,它“吸引了最渺小的造物的倾听”,也使幽深的森林褪去往日的阴森与寂寞。徐玉诺说,“诗人正像是一至高无上的艺术的祭司”,无关风月,只是爱了这奇异的乐音和长长短短的诗歌,它们是我对于“美与艺术”的第一次记忆。
信函们听说过奇迹,却没见过春天的苍穹之下,文字的奇迹。闻一多打开第4个信函,亲切地说,我也在期待奇迹的出现,期待他们不受生活的束缚来到我的眼前。只要奇迹一出现,他就绝不会浪费力气去“剥开顽石来诛求白玉的温润”。在那个贫乏的年代里,诗与美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他渴望奇迹的名字——美。它不是一个美丽的妙龄女子,而是“戴着一个圆光的你”,是锤炼数次的文字经诗人升华后的造物。蓝色的苍穹伏在诗人的案边,抽出火焰的飘带,展开希望的红色,那是贫乏的时代里难能可贵的色彩与诗思。
第5个信函越走越远,来到了另一个国度的康桥。诗人徐志摩正立于康桥边,接受康桥的洗礼。他像痴鸟一般,痛苦和欢乐浑然一体。他把自己心里最柔软的地方抵向花刺,口里不住地吟诵星月的光辉和人类的希望。康桥变换了信函的模样,也改变了诗人的气质。诗人投以忧郁的微笑,在简洁的破晓时分,写下“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那晚的康桥是沉默的,西天的云彩成为他最后的背影,可轮回的生命之外,还有一束弥留的霞光、一声耳语的别离。
秋歌散尽,万物进入永恒。第6个信函仿佛看见半阕枯涩的诗歌,于是他便去追寻那和谐的半阕。梁宗岱站在暮霭的茫昧之中,看着“温软的影儿恬静地来去”。影儿走进诗人,谛听他的灵魂。悔恨与沉思交叠,狂热与冷静相撞。最后,诗人找到了最契合自身灵魂的方式:“虔诚地,静谧地,在黄昏星忏悔的温光中,完成我感恩的晚祷。”再渺小的人类,也可以拥有长长的的影子。但影子不会说话,如同信函的火漆不会自己松软。多少只野兽从内心深处跑出来,突兀地出现在某个早晨,它们不是为了恐吓而咆哮,而是为了唤醒沉睡的灵魂。
有一天,熠熠的星辰从树上轻轻落下来,落一城的雨,但也不觉着阴郁。那是大海的一个梦,也是诗人笔下的梦。冯至一生都在用生命感受漫长的岁月里“彗星的出现,狂风乍起”,彗星与狂风,以及狂风与彗星,彼此都相得益彰。即使容颜屈服于时光的雕琢,灵魂也不会舍弃每一次赞颂,和慢慢消逝的启示。冯至从自己的生命里抽丝剥茧,“我们把我们安排给那个未来的死亡”,因为一切喧嚣最后都会凋落,惟有渺小可以成就伟大。我打开最后一封信函,告诉诗人:我已经准备好领受“狂风乍起,彗星的出现”。
7个信函完成自己的使命回到月光身边,他们早已不再单薄,即使看上去空空如也,却满是丰盈的智慧。
张爱玲说:“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我刚好遇上了最好的诗人和他们的灵魂之作。如果今晚又是一个孤独而晴朗的月夜,我将拂去一切缀饰,准备迎接下一个信函。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学生 许渝倩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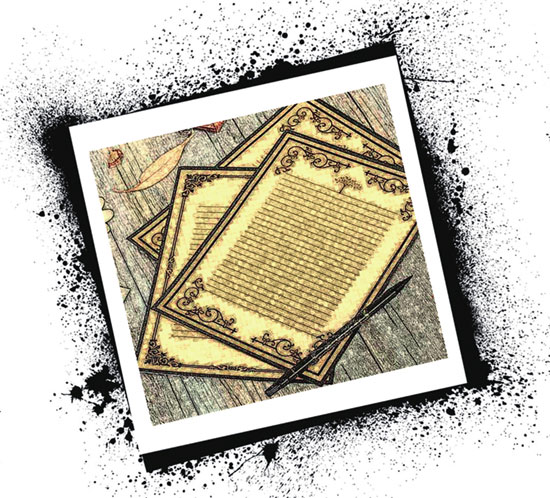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