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你为什么来这里?”
“我来做志愿的。”
“你对你爷爷奶奶也这么好吗?”
“我……”
“你肯定是个好孩子,能来看我们的都是好孩子。”
二
我们还是三五成群地去往社区服务站,这种形式已经是一种传统了,而每次随行的都会有新的面孔,他们多数是大学在校生。同行的人一路少话,人本就不多,一前一后走着隔了几步路,领队的时不时回头望两眼,可脚步依旧匆匆没有停下。我们下了地铁就接着步行,穿过几个红绿灯路口,不久我们就到达了目的地。
这里的服务站成立多年,是专门服务于周边小区居民的一个公益机构。大学生志愿服务队和这里长年有往来,学生们大多是流动的,老人多数是不变的,新的常住老人会加入进来,但也有人驾鹤西去。
我总以为待在养老院这样的地方的老人多数是郁郁寡欢的,后来发现,这个服务站毕竟和养老院的性质不太一样,这里更像是一个老人娱乐生活的社团。除去了日常生活起居所带给生活的乏味,剩下的就是交给时间的各项娱乐活动,用他们老人的话来说,只是为了消磨时间罢了。而同行的伙伴也有不太情愿的,对于他们来说是消磨时间,对于我们是奉献青春,然而,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不是来拯救世界的,我们只是想做件好事,做好这件事就够了。有时候,只有当你在做一件看似无意义无回报的事情时,你才能透过事情的表象看到人间。
三
有人说,一位老人,就是一座图书馆,进入老人的世界,像是探寻知识与秘密的宝藏。
从小,我就爱听爷爷奶奶们讲述以前的故事。在他们看来是陈旧的回忆,对我来说却是一个新的天地。
他们娓娓道来却在平淡中又夹杂着人生的况味,听到至深至情处,我竟久久不能回神。我自幼觉得自己很招老人喜欢,因为我总是会不厌其烦地听他们说各种事情,小到柴米油盐的琐碎,大到他们的岁月过往与国家的栉风沐雨。
在我看来这里的老人是幸运的,他们身处繁华的闹市,眼界是开阔的,选择是多样的。毕竟,有这样的社区服务站将一群老人们聚集在一起,那些只有安静才能体会到的深层的孤独也会离他们远去不少吧。
走进他们,发现这些老人的脸上总是带着微笑,没有任何烦恼似的,不知是不是氛围所致,即使再内向的老人也会时不时附和几句调侃一番,也许这才是健康老人的正常的生活状态吧。在他们的身上,我看到并没有太多自己所认为的暮气感,他们似乎重返了青春,依旧对生活充满热情,对世界有着新的向往。
四
活动总是多样的,这一次我们教老人们如何玩转手机。
有人喜欢将老人和小孩相提并论,但其实在很多方面,老人在各方面都是逆生长的,唯有那些沉淀在岁月里的东西越堆越多。就以使用智能手机为例,孩子似乎有一种对智能产品天生的感悟能力,无师自通,很快就能玩转各种App。而老人家则不同,首先是好奇心不够强烈,学习欲望总是会在自我否定中消散。其次就是,很多老人家似乎不太愿意麻烦别人,怕别人觉得自己多事。再则老人家到了这种耄耋之年,似乎进入了一种老庄的思想,无为,无欲,顺其自然,不强求的心态。于是乎,本是以教会老人使用手机为最初目的,最后索性和老人聊起家常来。
坐在我旁边的是位七十多岁的老人,讲话流利标准。老人说,她曾经做过教师,现在退休了。在她八九岁的时候,家里重男轻女,不让女孩子上学,那个时候的她非常羡慕那些可以上得起学的孩子,尤其是当他们考上大学去了城里回来后那神气模样,让她久久难以释怀。她曾和父母倾诉过心愿,可是家里人不同意,然而她那时的反抗精神极其强烈,千辛万苦之下终于求得了上学的机会。但求学路并没有她想象的那么顺利,一边是来自家人的压力,一边是来自各种家务琐事的繁忙,她对学习开始有些力不从心,成绩一直不高不低。
此时,有位老师出现了,改变了她的一生。那位老师非常鼓励她,曾对她说,现在你就努力好好读书,家里的事情先放在一边,你想学就好好学,我很看好你。于是,带着这种鼓励,她一路考上了初中高中,但是到了最后,因为复杂的原因她还是放弃了高中学业。至于是为什么,老人说自己也记不清了。有些原因可能被自己掩盖了太久被淡迹了,或许是面具戴久了难以摘下,也就真以为是那样了。之后,在一次难得的机遇之下,她进入了深圳的一个学校教书,带着自己那位老师的影子,怀揣着一种神圣的责任感,她励志要做一名好教师,坚持传授知识直到退休。回过头来,老人的话语中没有任何悔意,似乎走的每一步路都是自己所做的决定,她说,现在她依旧很感谢当初的自己。
我静静地听着,看着老人的双眼总能感受到那汪潭水的波动。
往年的故事,总是让人唏嘘感叹又回味无穷。看着老人平静的神情与她那沧桑的面孔,像是在看一本泛黄的书上流淌的文字。
五
“对你爷爷奶奶也这么好吗?”
“我……”
好吗?只要愿意听他们讲话就是好吗?
我不敢回答,如果是这样,那我应该是个很差劲的孙女吧。我已经很久没回过家了。
母亲曾说,我就当把你嫁出去了。听了这话我很难过,虽是戏说,但却很现实。自从上了大学,我对家人的陪伴越来越少,这种少不在于时间的长短,而是在于密度。在这里,我可以很自然地和这些仅仅见过几次面的老人嘘寒问暖,短时间内高密度的语言思想交流,可是却难以对家里人说一些肺腑之言,这是什么情感障碍呢,我至今都想不明白。我曾以为只要我努力学习取得好成绩就是对家人最好的回报,一切以自己为利益的行为总是那么理所当然。
身为志愿者,于我来说,甘愿奉献之余更像是在自我救赎。
这里的每一位老人,渴望和别人倾诉交流,他们不想终日无所事事,一个人一旦没什么事干就特别容易难过。身旁的老人时常讲着讲着停一会儿,我知道她在疯狂地搜罗自己的故事,继而滔滔不绝。
在她的身上我总能想起自己的奶奶,她也喜欢对我滔滔不绝地说话,即使我总是难以听懂那些方言。此时的她是否还在田间劳作,我知道她不喜欢闲下来,人一旦忙碌起来就不会去想其他的事情。我总想着,或许现在的我多听一会儿他们的故事,也能弥补心中的那份愧疚吧。
这场救赎之路仿佛没有终点,或许志愿就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在与老人们相处的过程中,我更加了解了远在乡间小院的爷爷奶奶,还有我的父母。
我愿相信,远行是为了一场回归,这场救赎之路的意义对我而言就是要珍惜当下。
特邀编辑:董学仁
丁钟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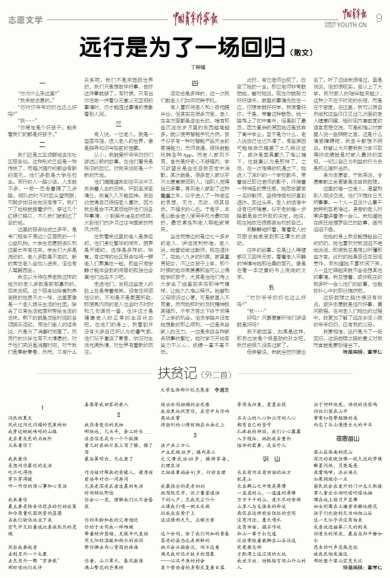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