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华栋,著名作家,现任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主席团委员。著有长篇小说《夜晚的诺言》《白昼的喘息》《正午的供词》等32部,系列短篇小说《社区人》《时装人》《十一种想象》等180多篇,共出版有小说、电影和建筑评论集、散文随笔集、游记、诗集等各类单行本100多种。多部作品被翻译成日文、韩文、英文、德文、意大利文、法文和越南文。罗晓光/摄
——————————
北京刷屏了。
在过去的一年,《北京传》《典故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和《故宫六百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相继出版。这三本新作的作者是大名鼎鼎的邱华栋、刘一达和祝勇,他们意在通过文学想象与历史书写完成城市记忆的复活与还原。城何以为城,又将如何演进,如何书写北京?与北京有着情缘的邱华栋、刘一达和祝勇在各自的写作中给出了不同的创意。
三千多年的北京城市历史,他们是这样书写的
“既然写《北京传》,我就要想到站在今天看待三千年时间轴的变化,最后落脚点还是在北京,所以我三分之一的篇幅都是写最近这七十年的变化。”邱华栋的《北京传》聚焦新北京:
在北京东三环中央商务区的核心区中,矗立起一座挺拔傲岸的建筑,从北京城的多个角度望过去,都能看见它,而它也在瞭望着你。
这就是中信集团的新大厦,俗称“中国尊”,在当前全世界最高的十座建筑中,位列第八。它高达五百二十八米,地上有一百零八层,地下八层。2019年大厦全面竣工,中信集团验收后入驻此楼,中信银行、阿里巴巴集团也入驻大厦。“中国尊”由此成为北京最高的人工建筑和新地标。
……
这座“中国尊”的落成,标志着北京的建筑高度跃上了一个新台阶。
京味儿文学作家刘一达笔下的北京历史是藏在“典故”中的:
北京城像一块四四方方的豆腐,中间是南北走向的中轴线,以中轴线为界,分为东城和西城,再以东西长安街为界分为南城和北城。
按照《周易》八卦的形制,南和北、东和西所有大的建筑是相对应的,比如内城的城门,西边有阜成门,东边就有朝阳门;西边有西直门,东边就有东直门;西边有德胜门,东边就有安定门;西边有宣武门,东边就有崇文门。
……
这种相互对应的关系,充分体现了“中正和谐”“天人合一”的礼法观念,也使都城变得恢宏大气、井然有序。这恰是北京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魅力所在。
祝勇作品的标签是故宫美文:
站在紫禁城巨大的广场上,望着飞檐上面青蓝的天空,我总是在想,紫禁城到底是什么?历史学家、建筑学家给出的所有定义,都不足以解释它的迷幻与神奇。在我看来,紫禁城是那么神奇的一个场域,是现实空间,却又带有神异色彩。它更像是一只魔盒、一座迷宫,或者命运交叉的城堡。因为它的内部,人影幢幢,魑魅交叠,有多少故事,在这个空间里发酵、交织、转向。紫禁城是不可测的——它的建筑空间是可测的,建筑学家早已完成了对它的测绘,它的神秘性却是不可测的,用深不可测、风云莫测来形容它,在我眼中都比用具体的数字描述它更贴切。它用一个可测的空间,容纳了太多不可测的事物,或许,这才是对紫禁城的真正定义。
点线交织的结构,如同一砖一瓦——这是邱华栋的《北京传》;作家的专注,学者的广博——这是祝勇的《故宫六百年》;引经据典,谈天说地——这是刘一达的《典故北京》。
三千多年的北京城市历史,他们是这样书写的。他们用一本20多万字的篇幅,完成了一项极具挑战和考验的创作任务。
城市是一个生命体,描绘它的成长史与空间变化
在这三部新作出版的前后,叶兆言写了《南京传》,叶曙明写了《广州传》,孔见写了《海南岛传》,上海作家小白正在写《上海传》……谈及《北京传》的写作缘起,邱华栋坦言:“我不是写这本书的当然人选。有一次我碰到作家叶兆言,我说叶老师你是写《南京传》的不二人选,你们叶家甚至四代都是作家,而且都在南京生活,好像你写,别人都没什么可讲。像我这样的新北京人,虽然在北京也待了二十多年快三十年,但是怎么样书写这样一个复杂的对象,触及它三千多年的历史,并不好处理,最开始真的有点蒙了,觉得应该由祝勇去写,我怎么把这个合同签了。”
“我写的是六百年,你这个要写三千年。”祝勇说。
在这样的压力下,邱华栋大概有两年时间一直在琢磨怎么写。“最开始我想写一个特别厚重的,我写了一个大纲,大纲完成以后得80万字,材料也很丰富,现在里面都没出现,比如植物、动物,比如整个下水道系统,还有一些1990年代的夜生活等,有一些更具文学性的经验。”邱华栋说。
“很多书写北京的书,它们更多写的是北京这个舞台上的人和事,但是对于舞台本身的变化不是太关注,城市作为一个空间,它作为一个生命体,它有自身的历史。” 邱华栋一下豁然开朗,“那么多写北京的书,写的都是舞台上的人和事,三千年的舞台怎么变化的,北京作为一个生命体,它三千年前在哪个点、空间有多大、它是怎么样在大地上像地基、像植物生命体慢慢成长,随着时间的推移长成现在这个样子,它的空间感的演变,我特别感兴趣。空间感的演变里面还有一个时间轴,时间和空间的架构出来,我形成了主章和副章的结构,就把这个事解决了。这样的话就比较简单了,空间的变化,描绘北京作为一个伟大的都城它的三千年成长史的空间变化。空间变化中的舞台上的人和事我非常有选择了,我可以少选择一点,也可以多选择一点。副章就是在一个平面时间轴的横轴上,以后可以不断添加,我现在只写了一两点,比如民国选两个小点,金代选两个小点,清朝选两个小点写一写,但这可以无限扩展,材料很丰富。所以我以这种方式一口气,一年多就写出来了。”
邱华栋坦言,为写《北京传》看了大量资料,《故宫六百年》也是参考书之一。“故宫是北京城里最不变的东西,从建筑结构上来讲它也是很坚固的。这样一个人类的建筑瑰宝,是不可能变化的。”
作家的历史写作,总会有一个“我”的存在
喜欢京味儿小说的读者,都知道“晚报”的刘一达,“我16岁就到工厂当工人,接触的都是老北京。后来又在《北京晚报》当了24年记者,骑着自行车串胡同,采访很多很多北京人,因此和北京缘分颇深。”
刘一达《典故北京》的书名就清晰地告诉人们,这本书主要是挖掘北京的故事、探索北京的传说,追根溯源,了解它的发展历程。北京的城门“门”字为何不带钩,北京的子午线在哪里,颐和园的昆明湖畔为何有一尊铜牛,老字号“稻香村”与“稻香春”的恩怨故事等。这些内容许多都是人们“知其然”但是“不知其所以然”的故事。
与刘一达一样,邱华栋也曾做过记者。刘一达的作品以地道的京味儿语言,钩沉数百年掌故人文,作为“新北京人”的邱华栋,他的写作在著名作家刘震云看来,“邱华栋的小说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别的作家写的是‘故’事,他写的是‘新’事。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他就能迅速把我们刚刚看见的生活,眼巴前发生的新事,迅速放到他的小说里。”
“故”事里的你,“新”事里的他,都有一个自我的存在。在祝勇看来,与历史学家或考古学家不同,作家进入历史写作,行文之中总会有一个第一人称的“我”存在。“华栋的《北京传》里面就有‘我’,尽管主角可能是萧太后,可能是完颜亮,可能是康熙、乾隆、梁思成等有各个层面历史人物在这个舞台活动,但是它始终有‘我’在。我写《故宫六百年》也有‘我’,这是不约而同的一个东西,作家始终离不开他个人的视角去看,而非纯客观的讲述一些知识。”
在博物馆里找灵感,去历史的长河中探索文物背后的价值,在城市的印记和发展中,寻找和发现不为人知的精彩故事,这是邱华栋、刘一达和祝勇书写北京的共同特点和写作体会。“从人的角度出发去写它,同时跟大的历史走向相结合,就会有一些不同的感受。”祝勇说。
纸上再现一座城的三千年——邱华栋做到了。邱华栋、刘一达和祝勇,与叶兆言、叶曙明、孔见等中国文学人,以自己的担当和勇气共同书写了一部城市大书。
责任编辑:周伟
本报记者 只恒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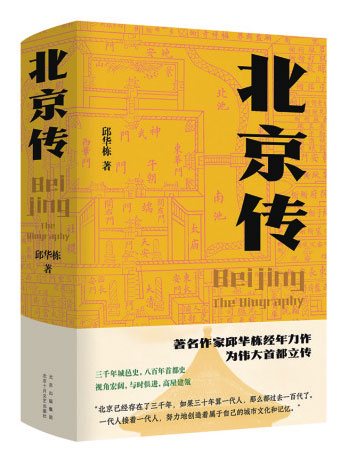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