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未如此后悔过。”她说。明亮的眼睛含着泪水,纤长的睫毛一颤一颤。手里的鲜花婀娜多姿,明艳动人,上面还挂着晶莹的露水。这是陈绵乡陈先生刚从鲜花店里买来送陈太太的。
陈先生和陈太太在一个25岁的酷夏相见。那时候陈太太还不叫陈太太,叫林小姐,是陈先生见过的长得最周正的人。
她穿着一袭红色长裙,明艳得就像她脸上的笑。
“陈绵乡先生?”她问。
林小姐的一双眼睛是最出彩的地方,仿若喉咙里含着未出口的话语都能从眼睛里掉落出来。
“是我。”陈先生的食指挠了挠大腿。他突然觉得家里安排的这场相亲也未必是坏的。
林小姐又笑。笑得像满船清梦,压的是陈先生心里的星河。
仿佛是害怕就此冷场,陈先生反问道:“林小姐?”
林小姐点点头:“你的名字真好听,‘郁郁多悲思,绵绵思故乡’。”
其实陈先生听不懂林小姐念的那句诗,但他喜欢她赋予的含义,“陈绵乡”三个字因为她的诠释万分生动。
两人沿着护城河缓缓地走,河里流淌的水就像两人的爱情。
林小姐其实不相信一见钟情之类的话语,什么爱啦,情啦,她只觉得这是只有在书页上才会出现的字眼。可是见到陈先生之后就不一样了。陈先生有着一双顶温柔的眼,大抵上说是全世界最温柔的也不为过。每当他用那双眼睛注视着她,她心里总有甜腻腻的味道,听别人说这叫坠入爱河。
后来两人疏松平常地交往,约会,一起去阒静的图书馆,一起吃齁甜的甜食。
陈先生买了间房子,一厅两室,主卧旁边的次卧被他改造成书房。高大又四四方方的红木书柜贴着墙角。再后来林小姐就成了陈夫人。
陈夫人总说这间书房是要留给孩子的。
可最终两人没有等待孩子,却等来癌。
被推着进化疗室,又被推着出化疗室,输液,花钱。简单又繁复的小原子构成生活的大分子。
后来就是一张一张的病危通知书,一笔一画的签名。
陈夫人现在捧着那株花,一年前烫的大波浪早已萎缩,只剩下发根。她早已被癌症和化疗折腾得脱了形,与骷髅并无二致的身躯,眼睛里头的桃花水绝源,也唯有空白。
她啜泣:“我好后悔,为什么没有在第一次进手术室的时候便死去。看看你现在所为我做的,毫无意义。”
陈先生瞪着一双眼睛,把陈夫人搂在怀里,尖锐的骨头将他磨得生生的疼,但他好像只有通过这种疼痛才能真情实意地感受到陈夫人的存在。
他望着她比墙壁还要惨白的脸说:“这一切都有意义,因为我爱你,所以比一切都有意义。”
陈夫人哭得快要晕厥过去。
这已经不知道是第几张的病危通知书。陈先生瞥见那道紧紧咬合的门,哀莫大于心死。
他的爱人正躺在里面。他仍然记得她曾说过她曾形容过,就像是死神和医生的赌注,谁赢了谁就可以得到她,而她只能躺在那里,没有感觉,麻木地被人支配。
可她漏算了另一个人。每一次陈先生都站在那道隔开生与死的门前与上帝博弈。
有人说,死亡是件很奇怪的事情,有人渴求,有人畏惧。但它终究不过是一件小事,轮回里的一件小事。
陈先生驳斥,死亡意味着一个人存在的丝缕都被抹去,只有记忆才能证明一个人的存在。
随后,他又加大了赌注。
他没日没夜地祈祷,不吃也不喝。
可命运是个任性的人。
陈先生颤颤巍巍地在最后一张病危通知书上签字。
从此以后,只剩下绵绵相思了。
责任编辑:曹竞 毕若旭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学生 朱佳雯(20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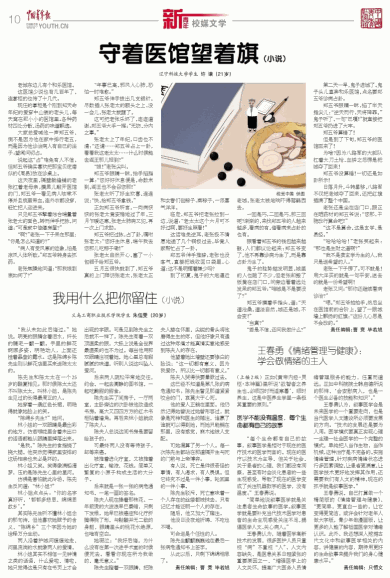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