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里尔克30岁之前写了一首《预感》,那是1904年,新世纪开始不久。到了20世纪40年代,这首诗有两个中文译本流传,后来的中文译本越来越多,更像一首地道的汉语诗歌了。
现在给你看一个你没读过的汉译,很短,不到十行:
我像一面旗子,围困在长天
我预感风来,让我不停地飘摆
低处的事物还和往日一样
门轻轻地开合,烟囱里没有声音
窗户没有颤抖,尘土躺在地面
我却预感风来,激动如大海
抛出自己,再跌回自己
并且以挣脱的状态,独自
一人,置身于伟大的风暴
对待《预感》这样容易理解的短诗,重要的就不是理解,而是进入诗歌去体验它。从普通读者到文化精英,每个人有自己的经历和经验,这决定了每个人体验的不同。
有自己的体验就好。
于我而言,我体验到的是在平静中预感到风暴的那种人,由于敏锐的感觉,由于准确的预见,常被称为先知者。里尔克是这样的先知者吗?他写这首诗时已经离开故国,而那个奥匈帝国不久就出现萨拉热窝事件,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再分解为许多国家,他出生的那个地方布拉格成为另一国的首都。
比起低处的事物,悬在高处的旗子,因为其高度,会更早、更准确预感阵阵风来。我们品读这首《预感》,能知道里尔克写它时,在静默中进入了体验的极佳状态,把自己化身为那面旗子。
对于写诗不久的人,这是很好的启示:开启一首诗的写作之后,等一些时间让体验到来,等一些时间让体验深入。
诗人不要急着写完一首诗,像画家不要急着画完一幅画。画家和诗人,都应该有了体验再沉浸其中,还要调整到感觉最佳。
再说个范例,里尔克的短诗《豹》,由于更深的体验和最佳的感觉,成为20世纪咏物诗的名篇,在世上广为流传。
它的目光被那走不完的铁栏杆
缠得这么疲倦,什么也不能收留。
它好像只有千条的铁栏杆,
千条的铁栏后便没有宇宙。
强韧的脚步迈着柔软的步容,
步容在这极小的圈中旋转,
仿佛力之舞围绕着一个中心,
在中心一个伟大的意志昏眩。
只有时眼帘无声地撩起。
于是有一幅图像浸入,
通过四肢紧张的静寂,
在心中化为乌有。
这是《豹》的第一个中文译本,冯至译的,很不错了。有人说,它是里尔克发明的咏物诗的代表作,也是那个世纪咏物诗的最高水平。我忽然想到的是,如果没有中国唐宋时期的许多咏物诗,这咏物诗的类型,也可以说是里尔克的发明。
宋代有人写过一首《梅花》:“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这里的梅花之上,寄托了作者的个人品行和志向追求。更早的唐代有人写过《在狱咏蝉》:“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侵。那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这首诗得到很多称赞,因为作者用蝉的困境写自己的困境,虽然还停留在对那只小虫的外部描述,虽然还没有进入它的内心,但那种情绪化的隐喻已经成熟。
个人认为,里尔克的《豹》很棒,是咏物诗的巅峰。
他进入了那只豹的体验。
他的眼睛是豹的眼睛,偶尔撩一下眼帘,有一幅图像浸入。更多时候,疲倦于那走不完的铁栏杆的纠缠,上千条铁栏杆成了眼里唯一的世界,除了铁栏杆什么也不能留在眼底。
他的身体是豹的四肢,在眼帘无声撩起时,由突发的紧张变为静寂。
他的步调是豹的步容,强韧又柔软的脚步仿佛是力之舞,只能在铁栏里绕着小圈子。
他的意志是豹的意志,虽然强大到使自己昏眩。
他的心是豹的心,能把外界的视觉刺激化为乌有。
里尔克描述了具象的豹子,就是巴黎动物园中的那只花豹,也描述了感觉中的自己,就是漫游世界却被命运纠缠的自己。他觉得自己的状况和豹子相似,于是便把许多现代人的感觉,如疲倦感、无力感、昏眩感、虚无感,都以豹子的体验表达出来。
但在我第一次阅读《豹》时,还有另外一些感觉。那时是20世纪80年代初,我和诗友当时能读到的现代好诗不过几十首,遇到这样的好诗就会细读深读。我和不同的诗友交流时,从这只豹子身上,也感到它的精神状态里,有某种从容,某种优美,某种高贵,某种信念,某种虔敬,某种苏醒,某种傲然。
这是在说,彼时里尔克写到的是他自己,此时我们读到的是我们自己。而在未来之时,诗友们读到的也许只有牢笼,被某时某刻的心理放大无数倍的牢笼。
短短十二行的诗,暗藏这样的体验,是不是有些神奇?
里尔克的体验从哪里来?按里尔克的说法,情感是我们早已有了的,我们需要的是经验。这经验的产生,要有诗歌创作的体验,再把这种体验带入到接触万事万物的过程。
“我们必须观看许多城市,观看人和物,我们必须认识动物,我们必须去感觉鸟是怎样飞翔,知道小小的花朵在早晨开放时的姿态……”里尔克说。他觉得,诗人必定要去感受、回忆、联想、体验身外的宇宙万物,从生命存在的深处与它们发生关联,方能达到物我合一的地步,如此经过长久的准备,才能产生一首好诗。
我们还要知道,里尔克在大学里读的是哲学和艺术史,他的某种哲学和艺术史观念,在诗中出现,大概是这样的:如果诗人像那只花豹一样,只能看到千条铁栏杆的时候,就应该返回了,返回到“眼帘无声地撩起”看到的“图像”,那原生态的图像,即走出主观观察的困境,回到客观观察。
里尔克的长诗短诗都写得很棒。
有人推崇他的《秋日》,觉得比《豹》写得好,让里尔克成了20世纪伟大诗人。
现在,我们也来看一下《秋日》,一首不用分行排列也诗意充沛的作品:
“神呵,是时候了,夏天已经太长/把你的阴影置于日晷上/让风吹过牧场//让枝头最后的果实饱满/再给两天南方的好天气/催它们成熟,把/最后的甘甜压进浓酒//谁此时没有房子,就不必建造/谁此时孤独,就永远孤独/那就醒来,读书,写长长的信/在林荫道上不安地/徘徊,落叶纷飞//”
如果你欣赏这首诗,就用前面说的里尔克的观念再读一次——感受、回忆、联想、体验身外的宇宙万物,从生命存在的深处与它们发生关联,达到物我合一的地步。
在我看来,里尔克最棒的短诗是《沉重的时刻》(另一个译本为《严肃的时刻》,可能更好),这首很有辨识度的短诗,让人一眼就看出里尔克的特质。
谁此刻在世界上某处哭。
无端端在世界上哭,
在哭着我。
谁此刻在世界上某处笑,
无端端在世界上笑,
在笑着我。
谁此刻在世界上某处走。
无端端在世界上走,
向我走来。
谁此刻在世界上某处死。
无端端在世界上死,
眼望着我
这个汉译,大约是我在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梁宗岱译诗集》里读到的,印象很深,深到骨子里了。此后主动想起它的时候不多,只是意识深层,与世界的联系多了一种认同感:天下人的痛苦都是我的痛苦,天下人的快乐都是我的快乐。
这首诗告诉我们,对世上所有的人和事物都要保持敏感和尊重,不要因为年轻,就把自己扩展成世界,忘了自己与万事万物之间的勾连。
这样的诗,写出来就是经典。
特邀编辑:董学仁
责任编辑:宋宝颖
满堂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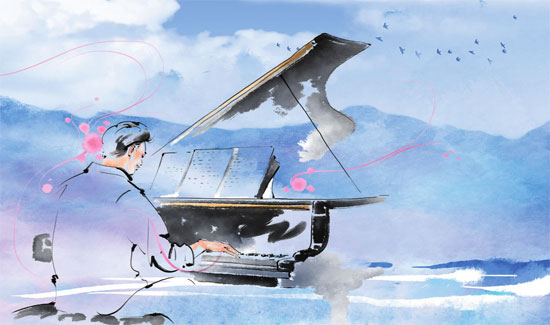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