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望舒有一首小诗,小到只有四行,标题是第一行的前两个词语,《我思想》。全诗如下:
我思想,故我是蝴蝶……
万年后小花的轻呼
透过无梦无醒的云雾,
来振撼我斑斑的彩翼。
这小诗没有让人惊异的那种优秀,比如中国古代的《登幽州台歌》就让人惊异,陈子昂写道:“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如果诗人早一千年去,幽州的那个台子上堆着黄金招聘贤才;如果诗人晚一千年去,那个台子只剩下土丘,什么也看不到了。他去的时候台子还在,但招聘贤才的事情没有了,所以他才能有深度感叹。当然,这也是陈子昂写得好。在他前后登幽州台的数十位诗人,怀才不遇的占多数,却没有像他那样独立苍茫,直接呼出万古落寞的情怀。
我觉得,时间的纵深感给了他一首杰作。这句话可以反过来说,他给了时间的纵深感一首杰作。
写好一首小诗不容易。
写蝴蝶也不容易。
从古代开始,写到蝴蝶的人不少了,比如李白写蝴蝶,杜甫写蝴蝶,都停留在事实的描绘。苏东坡写蝴蝶轻灵一些,李商隐写蝴蝶迷蒙一点,都算不上深入。还有一位有名气的诗人写了三百首蝴蝶诗,都不是传世之作,湮灭在岁月里了。明确地说,他们没有他们的文学前辈庄子在一篇散文里写的蝴蝶更好。
这样看来,戴望舒写的蝴蝶还真不错,起码有时间的跨度和纵深感,小花发出轻呼,已然万年之后,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或者已经发生。
这是戴望舒利用时间跨度和纵深感的第一种情况,突然间伸延到遥远的年月,可以容纳诗人的情感和思绪,也给读者发挥想象的余地。
读这首《我思想》,我想起戴望舒的另一首诗,标题为《寻梦者》,也有时间的跨度,表现方式却不一样,是一点点伸延的,显得充分,显得清晰。
你去攀九年的冰山吧,
你去航九年的旱海吧,
然后你逢到那金色的贝。
它有天上的云雨声,
它有海上的风涛声,
它会使你的心沉醉。
把它在海水里养九年,
把它在天水里养九年,
然后,它在一个暗夜里开绽了。
当你鬓发斑斑了的时候,
当你眼睛朦胧了的时候,
金色的贝吐出桃色的珠。
把桃色的珠放在你怀里,
把桃色的珠放在你枕边,
于是一个梦静静地升上来了。
你的梦开出花来了。
这首诗像是童话,接近于黑塞式地写给成年读者的童话,很美,很神秘,很多意境。
岁月逐渐伸延,四个“九年”,依次打开。“九”是个位数中最大的一个,在这里是实值又是虚值:中国人喜欢用“九”表示比它更多的数量。即使是实值的四个九年呢,也不算短了,戴望舒四十五岁时病逝,只活了五个九年,从他有力量攀冰山开始,他的一生短于金色海贝绽开的时间。一位喜欢做梦的诗人,没有等到梦里开花,这让现在读诗的我们,同样遗憾。
这是戴望舒使用时间跨度和纵深感的第二种情况,时间跨度是一层层伸延的,表现很充分,读着很清晰。
我们回到前一首诗《我思想》。应该说比中国古代写蝴蝶的诗好了一些,因为现代人眼界和心界开阔,情绪复杂,感觉新鲜,思想多维,感情多彩。
这个优势,很多现代诗人没有好好发挥,也不知道怎样去好好发挥。写诗的人很多,却没有一所专门的诗歌学校教他们进阶,于是,他们领会诗歌的妙处容易,写出这种妙处很难,自然也不知道如何表现自己的复杂情绪和诸多新鲜感觉,这才是超越从古至今诗歌前辈的关键。他们的作品偶尔出现灵感的闪光,却缺少多维多彩的思想情感,这也是个关键之处。
假设他们就是戴望舒,现在三十二岁,想写一首《我思想》,那么他们怎样写这首诗?
有个简单的方法,他们要为抽象的思想找一个客观对应物。这个观点是英国诗人艾略特提出来的:通过诗歌中的各种意象、情景、事件、典故的有机组合构成一幅图景,从而造成特定的感性经验,达到情与理的统一。戴望舒那一代中国诗人对这个人不陌生。徐志摩写过仿艾略特的诗,戴望舒请人全文翻译艾略特的《荒原》。
如果他们是戴望舒,想到的客观对应物是蝴蝶。这是容易发生的比喻,那蝶翼很像是书页。他写过一首《白蝴蝶》,“给什么智慧给我,/小小的白蝴蝶,/翻开了空白之页,/合上了空白之页。/翻开的书页:/寂寞;/合上的书页:/寂寞。”
用蝴蝶来表现思想,还有向庄子的致敬。庄子梦见自己变成了蝴蝶,栩栩飞舞的蝴蝶,梦醒之后怀疑自己是谁,到底是梦到庄子的蝴蝶呢,还是梦到蝴蝶的庄子?
第一行诗句写出来了:“我思想,故我是蝴蝶……”
像很多读者发现的,这可能源于法国哲学家笛卡尔说的“我思故我在”,另一中文译法为“我思想,因此我存在”。这警句般的第一行诗,确实加上了戴望舒的想法,这个存在是蝴蝶一样的存在。
接下去自然要描述蝴蝶。这只蝴蝶怎么写,才能表现出思想的状态?
大多数诗人都会这样考虑。但是要注意,思想的状态太多,几乎无尽。谁有描述思想整体状态的念头,只是徒劳妄想。他们只能用蝴蝶(或云卷云舒、怒海狂涛、万丈高峰、小溪细流等某一客观对应物),象征性表现出思想的某一状态。戴望舒就很聪明,不去描述他的思想如何,不去描述他的蝴蝶如何,而是描述与蝴蝶相关的一个场景,就是这首诗的剩余部分,其实一句话:“万年后小花的轻呼透过无梦无醒的云雾,来振撼我斑斑的彩翼。”
这首诗最后一行,许多版本都是“来震撼我斑斓的彩翼”。我看到戴望舒的一页手迹,写的是“来振撼我斑斑的彩翼”,略好一些,不显生硬。在这一行之外,花,是云雾后面的小花,因为很小,它惊讶的叫喊是一声轻呼。而云雾,是无梦无醒的云雾。这样一来,全诗大都是用轻柔的词语写轻柔的场景。
“无梦无醒的云雾”,我有个感觉,这像是戴望舒赋予的命名,那样的云雾不在梦里,不在醒时,无所谓梦,无所谓醒,已然超出了梦与醒,是一个新的范围。既是写蝴蝶的诗,我觉得这可能消解了庄子梦蝶后“我是谁”的问题:既然无梦无醒,提出那个问题的条件就失去了——有梦、有醒的时候,才能有那样的疑惑吧?
这首诗写完了,写出了诗人思想状态的一个方面,或者说他诗歌的一种特质:蝶翼一样轻柔而美丽。
二十世纪早期的中国诗人,除了中国诗歌的审美传统,还融入了世界上各种思潮流派,成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当时几位代表诗人,1897年出生的徐志摩,留学英国时开始写诗,受华兹华斯等人的自然观和浪漫主义影响较多;1899年出生的闻一多,留学美国期间接受了惠特曼等人诗歌中的直觉、超验、神秘、浪漫和写实观念。1905年出生的戴望舒,在法国留学接受了马拉美等人成熟、完整的象征主义。
象征主义的诗,当时读懂的人不多,因为诗要传达的是什么意思,作者隐藏起来了,不告诉读者。当时有位批评家指出,诗歌传达思想感情有不同方式,写实主义是描写出来的,浪漫主义是呼喊出来的,而象征主义是烘托出来的。
比如《我思想》,比较难读,比较耐读。
特邀编辑:董学仁
责任编辑:宋宝颖
满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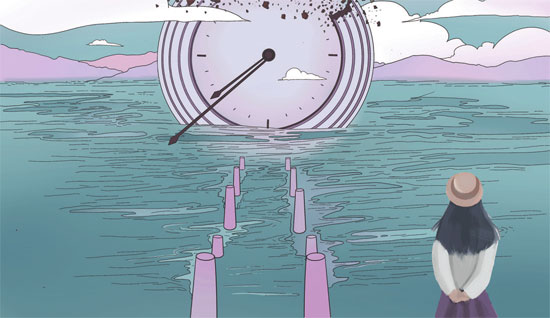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