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电影主角李红迎着夕阳与晚霞,站在山巅,扔下那张ETC卡的时候,她是自由的、独立的、勇敢的、热烈的;当李红身着一袭红裙,自驾行驶在公路上时,那正是她生命如红玫瑰般绽放的瞬间,是掌握人生主体性的力量。正如影片开头那句“我用了那么多年,才走到这儿,谁也别拦着我。”是李红告别旧我的心声,这延续了140多年前娜拉出走的自我觉醒意识,以及女性真正实现了出走的现实意义。
第一次出走——从原生家庭的束缚中脱离出来。对于李红来说,“结婚”意味着可以拥有自己的时间和空间,可以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弗吉尼亚·伍尔夫曾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谈到这个“房间”对女性的意义,她所说的“房间”,不仅仅是物理层面上人类生存所需的居所,更意味着精神上的自由空间,思想在此漫游,灵魂在此升华。当李红骑着自行车奋力穿过市集与人群时,眼中充满了对新生活的向往与期待,她奋力冲破原生家庭带来的不平等的束缚。
第二次出走——从丈夫的冷言恶语和生活的鸡毛蒜皮中走出来。从原生家庭到自己组建的小家,李红开始为自己想象中的生活而努力,开始像邻居马婕一样增添生活仪式感。但其实并不像结婚前所想象的自由,尽管受到外力影响,她失去了工作,但李红深刻意识到,经济独立对女性的重要性,于是她从未放弃任何机会。多年后,李红本打算在女儿预产期之前去成都参加一次同学聚会,但由于预产期提前,一次在内心积攒多年的出走计划宣告失败。于是,在孙子大宝、二宝上幼儿园之前的3年,李红再次被家庭的琐事“框”住,再次承担了家庭关系中的牺牲者。但一次次的隐忍与自我牺牲,换来的不是丈夫的暖言暖语与力所能及的帮衬,而仅仅因为小辈想要换掉李红那部摔坏的手机,他便以狭隘心胸反复质问李红“你图啥你自己知道”。此刻,压抑已久的情绪达到了顶峰,她将水果刀插向了自己。
母亲角色在家庭关系中的矛盾性再次显现。每个人都离不开母亲,但没有一个人真正关心过母亲的内心,以至于母亲患上了中度抑郁与焦虑。于是她乘坐公交车,穿梭于城市的立交桥,但这次出走对李红来说,至关重要,她了解到了“自驾游”,拿着那块象征自由与勇气的丝巾,打破了乏味生活的困局。李红开始一边考驾照,一边努力赚钱实现买车的计划,可是当她兴致勃勃拿着驾照回家准备小小庆祝时,却以家人的冷漠表现而告终。影片中的第一种平衡关系出现,“母亲”这个角色与家中的丈夫、女儿、女婿站在天平的两端,只有她一味地付出才能够换来全家工作与生活的和谐。
第三次出走——一个女性真正意义上实现了自我的翻盘。她不是谁的附庸品、也不是谁的保姆,她属于自己,她属于任何地方,她和每个人都是一样的。正如“妇”这个字的演变,代表了女性地位的提升,古字形“妇”是由女和帚构成,表示女子拿着扫帚打扫卫生,承担家务。而今天,“妇”字早已脱胎换骨,我们从中能感受到女性的勇敢和力量。以李红为代表的女性,再次抒发“我也想有我自己的事情,我跟你们是一样的”。在家中,李红自驾游的装备只能放在阳台不起眼的角落,但就算家中属于她热爱的部分只有一小块,那也是她对待生活的积极态度,是支撑她走下去的救命稻草。她的生活包围着无数琐碎的声音,那滴滴答答的乒乓球声、水滴声……已经掩盖和浇灭了她对生活所有的激情。这一次的出走,是为自己而活,为自己的热爱与梦想而活。
影片中展现了不同年龄段女性的生存困境,她们从小会面对不公平的对待,长大后会面对育儿与工作的平衡等问题,很多事情在无法选择的情况下,再次走上每一代人所经历的闭环。“生活就像一场无法醒来的噩梦,我在其中拼命挣扎,却找不到出口。”这正是女性所面对的现实,影片也以实际行动来告诉女性如何走出困局、如何追求自我。在现实生活中,越来越多的女性将自己的经历通过各种媒介形式表达与抒发,拥抱自己所热爱的一切,呐喊出“我不想再这样活下去,我要寻找自己的光。”
《出走的决心》是李红出走的故事,但更是女性群像在生活中的展现,她们会在大路封闭的时候,探索小路、野路、山路,反正总归是能走出去的。影片中李红的原型正是现实生活中的苏敏,她开车一路疾驰,跨越千山万水,走遍祖国的大江南北。她开始把自己还给梦想、还给一切值得的事物,她不再等待,不再被“框”住。此刻,她还在路上,她们还在路上……
责任编辑:宋宝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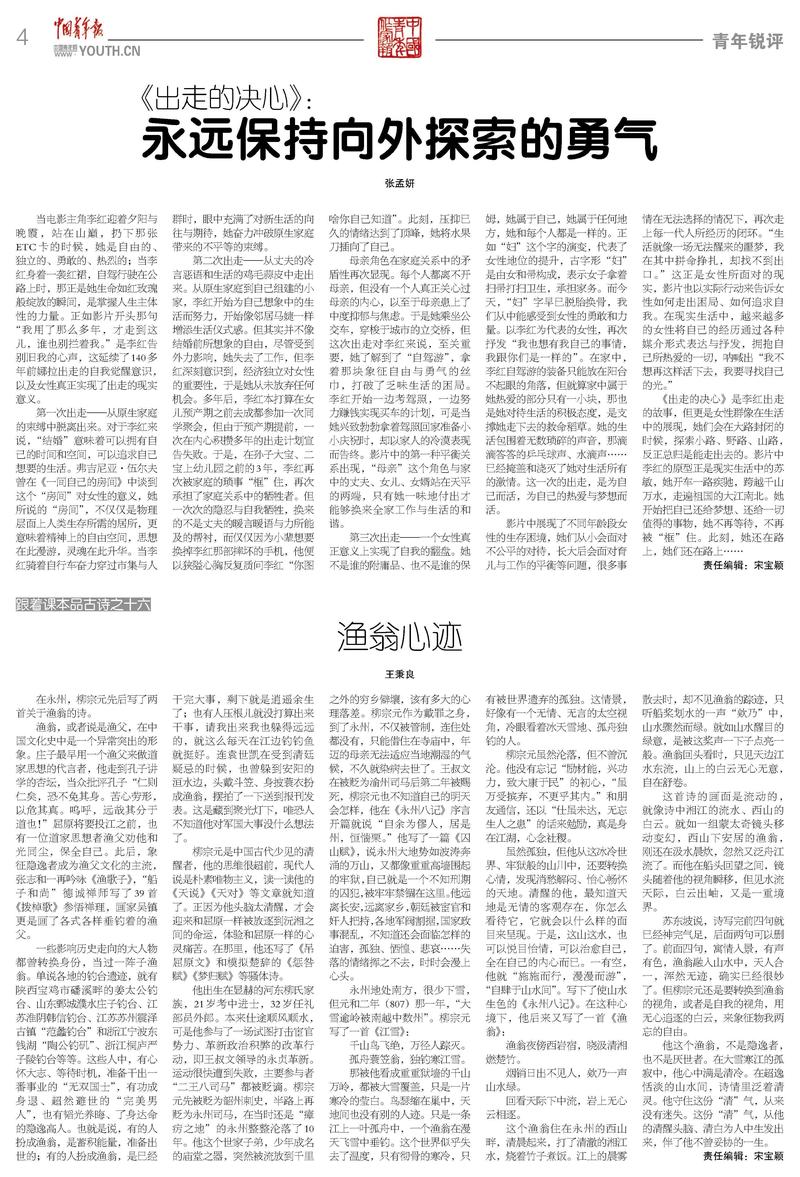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放大
放大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