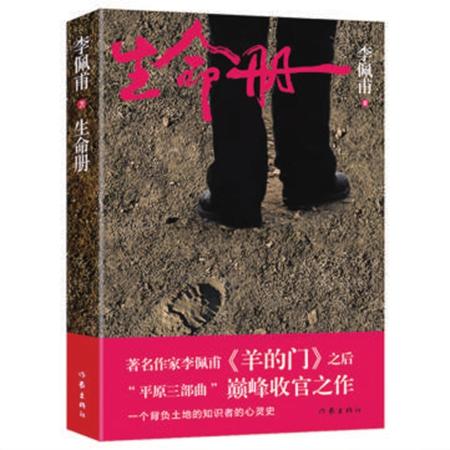
诸多作家在书写乡土文明时,无不在对时代背景进行理性分析的同时,与个体的感性叙事形成互补,共同构建出乡土社会中人物命运的生存哲学。《生命册》这部作品里,亦展现着城市生活与乡村世界对立互参的情感纽带。全书以吃百家饭的孤儿吴志鹏的视角,讲述了无梁村不同人物的命运起伏。采用章节叙事法,将当下空间与历史空间交织融合,以第一人称视角对人物进行俯瞰与剖析,展现出人性在不同境遇下善与恶的复杂多面性,从而记录时代变迁中形形色色的命运轨迹与生命意蕴。全书在吴志鹏对于故土的逃离再到回归的自省中串联起蔡国寅、杜秋月、梁五方、虫嫂等一系列人物的命运悖论,在时代变迁的进程中,揭示出当代城乡发展的基本走向与厚重的乡土社会人文精神。
独特视角的书写与交织
法国文学批评家热拉尔·热奈特将文学作品的叙事视角分为内聚焦、外聚焦以及零聚焦三种。本书放弃了传统聚焦叙写手法,以从前20年与后30年的时空片段交替呈现的独特视角展开叙事结构,依托于主人公吴志鹏的回忆与讲述,从自我叙事“我是移栽进城市的一粒种子”平白铺叙展开。由无梁村吃百家饭的孤儿成为省城大学老师的转变让他深刻地认识到:“要想顺顺利利地在城市生活,必须要有三要素:身份、单位、关系。这三者缺一不可,如果没有身份,没有单位,再没有关系,那么就成为了一个漂泊者。”因此他急切消解乡土身份带来的差异,去学习城里人应有的行头与习惯,却在无梁村乡亲们一个接一个令人胆战心惊的电话里无法承受金钱与人情的重担而选择了逃离。随后进入商界的他收获了金钱、权力、地位,享受着曾经梦想得到的一切,但他的心是空的,始终与城市存在着隔膜。无数的虚荣让他快要忘记归属、忘记源头的根时,面对已故老姑父源源不断“见字如面”匿名信的提醒,他才发觉“我与这片平原上的无梁村的土地是永远没办法分离的。”他失去乡下人的自我,向城市人转型,但又不能完完全全与城市融合在一起,也不能彻彻底底与乡土亲近。30年后再次踏上故土,与乡亲们一起为老姑父立碑时,他把自己比作“一片干了的、四处漂泊的树叶”,他不知道他还能不能回到树上,他叙述:“我的心哭了,也许我真的回不来了……”
作为这样一个从农村强行进入城市,最后精神无法回归的城乡人,身份认同在适应环境的过程中受到阻碍,在外来异化中被扭曲,在自我与他者之间徘徊,最后不断被边缘化,被迷失。这种认同的双重化建构过程引发对如何重塑故土记忆的拷问。正如周宪在《全球化与文化认同》一文中说到“乡愁或怀旧作为一种集体历史记忆的重现,是对美好过去的追怀,在这种复杂的过去重建过程中,它满足了今天看似比较单纯的对往昔的忆念。”
书中结尾部分,全村人为老姑父举办了极其隆重的迁坟仪式,集体怀念老姑父,也缅怀过去的乡土记忆。乡村和城市作为人类生存的空间,承载着现代人的精神依托,当人们面临人情、欲望的困境,遭受城乡文明冲突带来的精神异化时,对老姑父的缅怀亦是安放精神漂泊下寻求救赎的一个缩影。
个体宿命的失衡与重构
书中人物无一不走入了自己理想生活的对立面。老姑父蔡国寅以英雄连长的身份与在校学生吴玉花不顾世俗羁绊而结婚,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随着众人艳羡目光的褪去,与吴玉花勾织的“成为一个军官夫人”的爱情产生落差,便出现了无休止的争吵。他作为“将印章挂在腰上”的村支书,在一次又一次的运动中坚定地站在被迫害人的一面,以自己的威望庇护着他们,却在年老时中风以至于无法对生活进行自理,整日坐在村口犹如一张风干的老树皮。由于前期他对家庭的漠视,妻子嫌弃他、谩骂他,女儿憎恨他、嘲讽他,后来想买个“可以听听国家声音的半导体收音机”都无法如愿,甚至在其死后,还传出脑袋被女儿埋进花盆,养成价值百万的“汗血石榴”的流言。
这一具有命运悖论的叙写在高知分子杜秋月的故事线中也同样相似,他从清高迂腐的老师“滑铁卢”成粗俗肮脏的“臭老九”,在众人说和中安于现状,娶了村里仰慕他的寡妇刘玉翠。获得平反之后开始对一心照顾他的刘玉翠心有不满,设套诱使她签了离婚协议书而远离无梁村。但在与刘玉翠的拉锯战中身心疲惫,终体力不支瘫痪坐轮椅,在婚后生活中如同一个摆设,晚年仰仗妻子而活。这种写作手法进一步将个体命运戏剧化表达,更显悲凉底色。在乡土基因与时代巨变的碰撞下,人物的走向不断被扭转,每个人都背负着自己的重担和融不进去的无奈,似乎这种在时代进程中支离破碎的命运,更能表达出乡土文明与乡土情谊的复杂性。
时代洪流的抗争与妥协
书中的虫嫂是一个无名无姓的袖珍人,被无梁村人称做“小虫儿窝蛋”。这样的称号含着一丝蔑视意味,让这样一个身形矮小肥胖的妇女无所顾忌,她一次次地偷拿公家财产、偷盗私人粮谷后被老光棍抓住,以性为交易作为日后苦难的解决途径。在面临粮食短缺、孩子挨饿的境遇下,“她便也不将自己当人看”了,次次习惯性地“宽衣解带”,破罐子破摔。这样的行为很快遭到了无梁村集体女性的报复围堵,她赤身裸体在雨中奔跑呼喊,男人们只敢默默相看。但虫嫂自身坚韧的意志,让她靠着这些不光彩的物资,加上拾荒贩卖所得将3个孩子培养成才,却因积攒太久的坏名声让3个孩子心存芥蒂,死前也落得无人问津的结局。
同样具有对命运抗争意识的手艺匠人梁五方因雕刻麒麟脊而名震四方、自立门户。由于他孤傲的性子在无梁村显得格格不入,众人对他的不满集体爆发,最终他辛苦建起来的用于结婚的房屋与其他所有财产被没收,而后走上漫长无边的上访之路。在平反解决之后他俨然已成为一个枯瘦如鬼的流浪者,打着“半仙”名号,靠四处给人算命为生。文中表述:“这也是我们家乡人的最大优点,那就是用戏谑的口吻,微笑着面对失败。”这种“戏谑”,既包含着对生存的无奈,也有对现实的挣扎。这些人物在时代洪流的裹挟下,如同长在平原大地上的一棵棵野槐树,经凛冽寒风吹压,依旧会在春野满山时盛开出簇簇槐花,飘出万千香意,谱写生命的韧性与永恒。以母爱为支撑活下去的虫嫂,坚持几十年跋涉北京、讨要平反文件的梁五方,他们薄弱的身躯里迸发出最大的力量,与命运不屈抗争。作者通过对无梁村百姓的命运塑造,真实展现在现代化冲击下对生命议题的深刻反思。
《生命册》是无梁村个体群像的鲜活图谱,更是关于人生、关于人性的思考。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中遭遇物质与精神的失衡时该如何安放自己的灵魂,书中恰当地采取了留白,这种留白亦是作者对命运未知的留白。我们何尝不是无梁村生命群像的一个个镜像,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一步一步地找寻属于自己的方向,或许正如罗曼·罗兰所说,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旧去热爱生活。
见习编辑:郑欣宜
责任编辑:周伟

 上一版
上一版





 放大
放大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