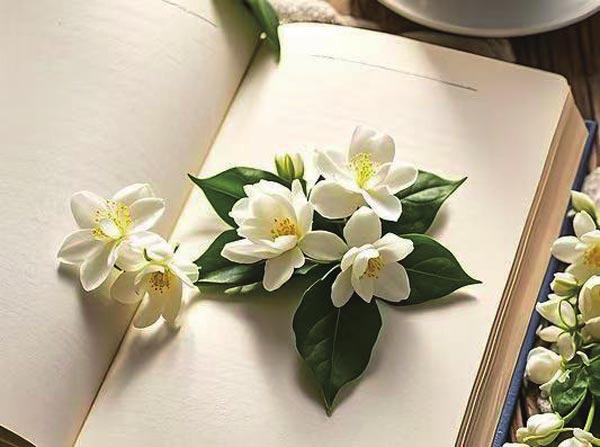
平常见到的栀子,都是重瓣的,花瓣繁多,挤叠在一起,就像揉皱的一团白纸。古人想象丰富,说它更像一只白色的蟾蜍,蹲守在繁枝绿叶上,仰望日月,就称它白蟾。让我惊奇的是,白蟾竟然是学名。栀子花除了花大色白,另一显著特征是,有浓郁的香味。郑逸梅在《花果小品》里说它为“夏花之最馥郁者,不可近鼻嗅领,因刺激太甚也。”汪曾祺则形容它:“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掸都掸不开”。有人不习惯这种直冲脑门的香气,以为俗气。明代王世懋《花疏》曰:“重瓣者花大而白,差可观,香气殊不雅。”杜甫的《栀子》诗:“于身色有用,与道气伤和。”也说栀子花的香气过于浓烈,与人们追求的平和之气不符,隐约间也有嫌弃之意。
不过母亲喜欢它。小时候,住的是土墙草屋,梅雨季节,家中地湿霉味重,蚊蝇又多。母亲会在堂屋的饭桌上放一碗水,水中养许多栀子花,有的正开,有的含苞待放,有的还是花骨朵儿。浓浓的栀子花香,弥漫开来,空气顿时清新了许多。母亲也将栀子花悬挂在我们的蚊帐里,一可祛除夏季汗味,二可防蚊虫叮咬,有助睡眠。母亲还将栀子花别在我们的衣襟前,戴在姐姐的发梢上,或放进我们的书包里。母亲说,身上有香味,老师会喜欢你,同学们也愿意跟你一起玩。
栀子花白如雪,又有清香,在炎热的夏季绽放,给人一种清凉舒爽的感觉。梁简文帝萧纲诗云:“疑为霜裹叶,复类雪封枝。”宋杨万里《栀子花》诗:“树恰人来短,花将雪样看。孤姿妍外净,幽馥暑中寒。”将栀子花当作霜雪一样看待,顿感凉意,暑气全消。可见夏日赏栀子是一件极惬意又解暑的事儿。
《群芳谱》中说,“众花之开,无不忌雨。”是说花都惧怕风雨。李渔在《闲情偶寄》中说:“栀子花无甚奇特,予取其仿佛玉兰。玉兰忌雨,而此不忌雨。”在李渔看来,栀子虽然平常,名气不及玉兰,却与玉兰相像。玉兰花开时最怕下雨,而栀子不怕。栀子花不但不畏风雨,相反,雨中的栀子更显精神,也更好看。古人发现了栀子这一与众不同的特性后,纷纷在雨中出门观赏,久而久之,雨中赏栀就成了一种时尚。王建《雨后山村》:“雨里鸡鸣一两家,竹溪村路板桥斜。妇姑相唤浴蚕去,闲看中庭栀子花。”韩愈《山石》:“升堂坐阶新雨足,芭蕉叶大栀子肥。”一场新雨过后,栀子开得更大,更舒展,更精神,一个“肥”字真是绝妙,更加彰显栀子不惧风雨的风骨和魅力。
月光下的栀子花更显素雅之色与清幽之香,月下看栀子,另有一番韵味。南宋女诗人朱淑真《水栀子》:“玉质自然无暑意,更宜移就月中看。”水栀子也是栀子的一种,叶小狭长,形似雀舌,花小,但数量极多。水栀子较矮,适宜盆栽。诗人认为,室内盆栽的水栀子花,最适合移到月光下观赏,其清冷的气质与月光相得益彰,更显高雅。自宋代开始,月下赏栀也逐渐流行起来。
栀子是常绿灌木,个头虽矮,却与松柏一样,也能抵抗寒冷。记得儿时的故乡,每到秋冬季节,所有的草木都凋落枯黄了,唯有田间的麦苗、园中的青菜、墙角的栀子还是绿的。黄朝荐《咏栀子花》:“何如炎炎天,挺此冰雪姿。松柏有至性,岂必岁寒时。”栀子的独特之处在于,她不仅以素花抗争于炎夏,还以茂叶挺立于严冬,因而兼具了莲花和松柏的品质,这是非常难得的。难怪杜甫也说:“栀子比众木,人间诚未多。”栀子花与众多树木相比,确实比较少见。
小区城河对岸是个城中村,一条新筑的柏油路,从中蜿蜒穿过。晚饭后,我喜欢去那里散步。路面很宽,路灯很亮,行人很少。路两旁是新栽的红叶石楠树,和剪得光秃秃的紫薇。路的尽头,有一株栀子树引起我的注意。说是一株,其实只有半株,另一半因延伸到路面上,有碍通行而被砍掉,刀斧的痕迹明显,白森森的伤口历历在目,让人心疼。它的根紧贴着路边,按理应当要被砍掉或被挖掉。我猜想,当时这里应是一户人家的庭园或菜地,栀子树就长在一角。因为拆迁征用,主人带走了全部物品,最后只剩下这株栀子树。有心带走它,又无能为力。连自己都寄人篱下,临时租的房子,实在无处安置它,只好狠心丢下了它。修路的人看到了它,也认出了它是一株栀子,从一开始就不忍心将其砍掉,一直保留着,等到路修好了,实在没有办法,只好狠心将其一半砍去,让另一半存活了下来。
劫后余生的栀子树,惊魂未定地长着,提心吊胆地开着。它的枝叶全部倾向路的外侧,不敢伸展到路的中央来。叶片稀疏微黄,花朵瘦小,花期也略有延迟。但还是那样的香,那样的白。
“无情移得汝,贵在映江波。”依旧是老杜的那首栀子花诗。无意将你移栽至此,又无情把你遗弃于此。难能可贵的是,你没有一点怨恨,也没有丝毫自弃,依旧守着那份初心,开一身洁白,吐芬芳气息,替我们装扮这可亲可爱的人世间。
见习编辑:赵小萱
责任编辑:周伟

 上一版
上一版





 放大
放大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