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城偶遇:抗战时空的印记
上海师范大学天华学院学生 方册(20岁)
来源:中国青年作家报
(2025年09月02日 08-09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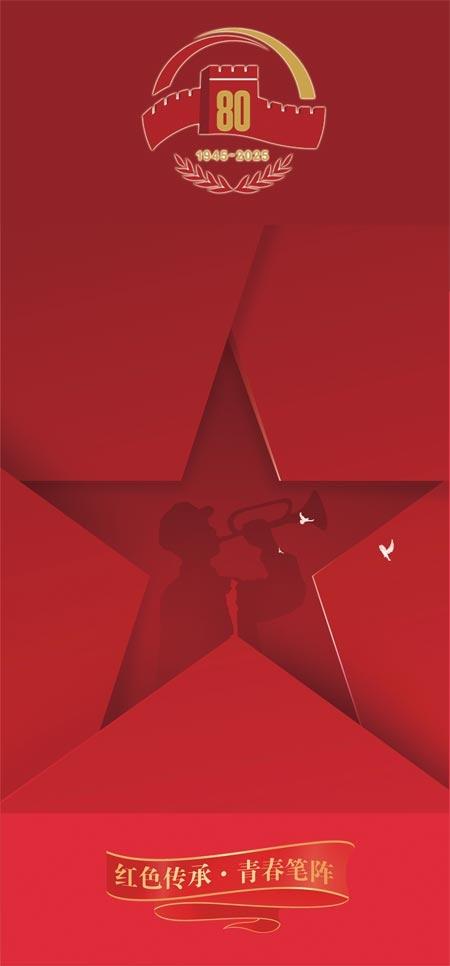
纪念,是为了更好地出发。
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回望那段血与火铸就的峥嵘岁月,我们更能深切体悟伟大抗战精神的厚重与深远。站在新的历史方位回望,抗战的枪声早已远去,但那份精神的光芒仍在照亮前行之路。它提醒我们,和平来之不易,复兴任重道远;它告诉我们,一个民族的力量不仅在于物质的强盛,更在于精神的坚守。
英雄并非天生伟岸,而是信仰让普通人作出了伟大的选择。在新的时代语境下,如何用文学与艺术的方式向先烈致敬、如何把信仰的力量传递给今天的青年,是《中国青年作家报》一直思考的问题。为此,从6月份起,我们邀请青年作家与编辑部共同创作“红色传承·青年笔阵”专栏,以笔为旗,让信仰的力量从历史深处走进人心,让坚守与担当在新时代青年的心中延续。
——————————
7月的合川即将入伏,空气中已经攒着燥热的暑气。我从上海回来没几天,高中同学就约着去铜梁洞——那地方在涪江南岸的铜梁山上,444.3米的海拔,是城区最高处,据说比城里要低三四摄氏度。
清晨,天刚泛白我们就动身了。铜梁洞的入口藏在一片翠柏里,石阶蜿蜒向上,黄葛树上的鸟叫混着蝉鸣,在山坳间此起彼伏地聒噪。
行至半山腰,二仙观的朱红山门从树影间透出来。这处明代为纪念张三丰师徒所建的道观,明清两度毁于战火,民国时重建,如今只剩几间简易殿堂和厢房。斑驳的朱红山墙间,门楣上“二仙观”3个金字被岁月磨得发亮,倒比别处多了层温润。檐角铜铃被山风拂得轻响,混着香炉飘出的檀香,在潮湿空气里酿出古旧的安宁。我们看了三清殿,赏过明清壁画与摩崖题刻,逛累了便坐在观外石阶上歇脚。
“那边好像还有块碑,过去看看。”同学忽然指着右侧摩崖下的平地。远远望去,一块墓碑依山而立,立在两层石阶上,后面围着简易石栏。我们踩着生苔的石阶绕过去,一方浅灰色的碑正对着山下城区,刻着“抗日将军杨瑞符之墓”9个红字。碑后是座小型墓冢,形制像川渝常见的土地庙,不足一米高。
“这个名字好熟悉啊!”我看着墓碑,喃喃自语,却又想不起曾在哪里见过这个名字。墓碑左侧刻着:“生于一九〇二年 卒于一九四〇年”。我努力回忆着这个名字,忽然想起3个月前,我在上海西藏路桥畔那座灰黑色的建筑里见过这个名字,还看到了墓碑主人年轻时的照片。
清明学校放假,重庆的父亲打来电话,让我回恒丰路老房子看看。这处位于闸北区的房子离苏州河不远,我很少住,望着窗外春柳飞絮,索性出门沿河岸走走。河上不时传来“哒哒”的马达声,驳船缓缓驶过。不知不觉走了两三公里,西藏路桥已在眼前。抬头时,前方一栋方形建筑斑驳的西墙突然撞入眼帘。
“上海怎么会有这么破旧的房子?”我暗自纳闷。虽说附近有自家的老房,却因从小随父母在外地生活,这一带并不熟悉。走到近前,见墙面由红与浅灰砖块拼成,左侧“四行”、右侧“仓库”的蓝色大字被风雨洗得发白,方才见的斑驳处,竟是密密麻麻的弹洞。
墙壁前,一块黑色大理石斜铺在地,上面是11个不锈钢大字:“上海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这竟是四行仓库?初中课堂上老师讲过,前几年电影《八佰》拍的就是这里的故事!我第一次发现,历史竟离我的家这么近。
我连忙预约参观,走进纪念馆。6个展区中,一进门的序厅里,谢晋元将军的巨型家书格外醒目:“巧英吾妻爱鉴……我神州半壁河山,日遭蚕食,亡国灭种之祸,发之他人,操之在我,一不留心,子孙无噍类矣。为国杀敌,是革命军人素志也……”字字凿凿,尽显保家卫国的坚定。此外,馆内还陈列着其他战士的家书。
玻璃柜里,《申报》号外泛着黄褐色,“闸北孤军四昼夜抗战”的黑体标题旁,印着士兵们用粮包筑工事的照片:底层门窗全被麻包堵死,二层以上窗口只留半扇,5-10米厚的牛皮、丝茧堆至天花板,像给建筑裹了层铁甲。解说员指着兵力部署图说:“1937年10月,谢晋元率524团1营官兵进驻此处,对外宣称有800人,‘八百壮士’由此得名。”
四行仓库纪念馆内,多组模型定格激战瞬间:日军顶铁板弓身逼近,弹痕累累,气焰疯狂;仓库各处,中国军人或瞄准、或装弹,钢盔蒙尘,面带疲惫却目光坚毅,紧扣扳机尽显守护决心。这些模型串联起战斗碎片,让当年的壮烈与热血清晰可触。
一侧展墙上,一名军官的肖像照片旁标注着“1营营长杨瑞符”。他身穿军服,戴圆形眼镜,眉眼不算英挺,却透着执拗。照片说明写道,其1939年所著《孤军奋斗四日记》中记录:“隔河民众见此壮举,齐声高呼‘中华民族万岁’,声震苏州河。”他还记录了战斗细节:“27日晨,尹排长率两班据守旱桥,敌占北站大楼插太阳旗时,战士们趴在民房屋顶射击,直到弹药用尽才撤回。”日记字迹有些潦草,墨水洇了好几处,像是他回忆战士鏖战时,因情绪激动而手颤所致。
这位四行仓库的营长杨瑞符,难道就是眼前铜梁洞墓地的主人?站在杨瑞符墓前,合川的山风穿过铜梁山的黄葛树林,沙沙作响。纪念馆里陈列的《孤军奋斗四日记》,是他在合川养伤时所写,字里行间的坚定似能穿透时空。1940年春,这位年仅38岁的将军在合川离世,葬于铜梁洞,墓碑朝着上海的方向。
下山时,我忽然惊觉,上海的家离四行仓库不过两三公里,合川的家到二仙观只需10分钟车程。这两个被战火串联的坐标,像两只大手,在我20岁的生命里轻轻一握,让我与那段遥远的历史有了奇妙的连接。
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四行仓库纪念馆建成开馆,杨瑞符营长的墓也同时落成。它们如两座不朽的丰碑,承载着那段刻骨铭心的历史。如今抗战胜利80周年已至,再回望这些纪念场所,意义愈发深远,中国大地的每一寸土地,都浸透着先辈们的爱国热血;他们当年用生命守护的山河,如今已成我们散步的寻常巷陌。那些刻在弹痕里的坚韧,那些埋在墓草下的赤诚,从来都不是博物馆里的陈列,而是流淌在血脉中的基因,在一代又一代人的生命里,悄悄完成着跨越时空的接力。
(指导教师:雷雨轩)
责任编辑:宋宝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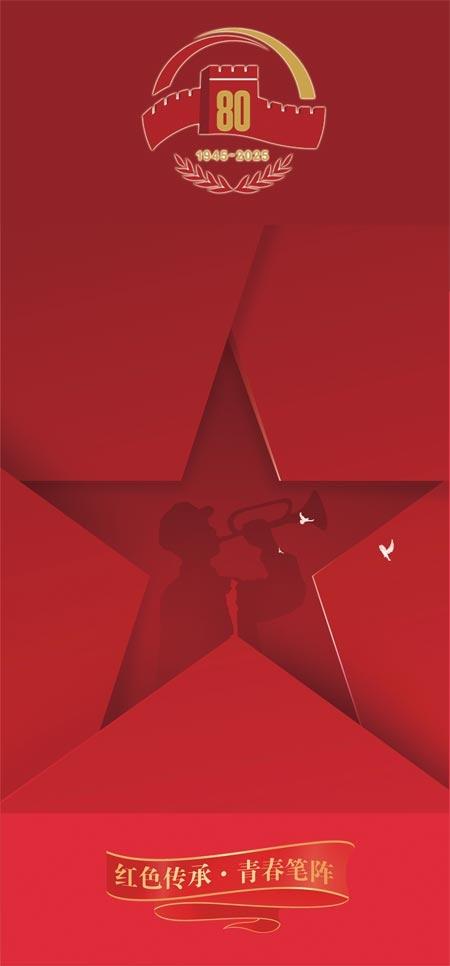
纪念,是为了更好地出发。
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回望那段血与火铸就的峥嵘岁月,我们更能深切体悟伟大抗战精神的厚重与深远。站在新的历史方位回望,抗战的枪声早已远去,但那份精神的光芒仍在照亮前行之路。它提醒我们,和平来之不易,复兴任重道远;它告诉我们,一个民族的力量不仅在于物质的强盛,更在于精神的坚守。
英雄并非天生伟岸,而是信仰让普通人作出了伟大的选择。在新的时代语境下,如何用文学与艺术的方式向先烈致敬、如何把信仰的力量传递给今天的青年,是《中国青年作家报》一直思考的问题。为此,从6月份起,我们邀请青年作家与编辑部共同创作“红色传承·青年笔阵”专栏,以笔为旗,让信仰的力量从历史深处走进人心,让坚守与担当在新时代青年的心中延续。
——————————
7月的合川即将入伏,空气中已经攒着燥热的暑气。我从上海回来没几天,高中同学就约着去铜梁洞——那地方在涪江南岸的铜梁山上,444.3米的海拔,是城区最高处,据说比城里要低三四摄氏度。
清晨,天刚泛白我们就动身了。铜梁洞的入口藏在一片翠柏里,石阶蜿蜒向上,黄葛树上的鸟叫混着蝉鸣,在山坳间此起彼伏地聒噪。
行至半山腰,二仙观的朱红山门从树影间透出来。这处明代为纪念张三丰师徒所建的道观,明清两度毁于战火,民国时重建,如今只剩几间简易殿堂和厢房。斑驳的朱红山墙间,门楣上“二仙观”3个金字被岁月磨得发亮,倒比别处多了层温润。檐角铜铃被山风拂得轻响,混着香炉飘出的檀香,在潮湿空气里酿出古旧的安宁。我们看了三清殿,赏过明清壁画与摩崖题刻,逛累了便坐在观外石阶上歇脚。
“那边好像还有块碑,过去看看。”同学忽然指着右侧摩崖下的平地。远远望去,一块墓碑依山而立,立在两层石阶上,后面围着简易石栏。我们踩着生苔的石阶绕过去,一方浅灰色的碑正对着山下城区,刻着“抗日将军杨瑞符之墓”9个红字。碑后是座小型墓冢,形制像川渝常见的土地庙,不足一米高。
“这个名字好熟悉啊!”我看着墓碑,喃喃自语,却又想不起曾在哪里见过这个名字。墓碑左侧刻着:“生于一九〇二年 卒于一九四〇年”。我努力回忆着这个名字,忽然想起3个月前,我在上海西藏路桥畔那座灰黑色的建筑里见过这个名字,还看到了墓碑主人年轻时的照片。
清明学校放假,重庆的父亲打来电话,让我回恒丰路老房子看看。这处位于闸北区的房子离苏州河不远,我很少住,望着窗外春柳飞絮,索性出门沿河岸走走。河上不时传来“哒哒”的马达声,驳船缓缓驶过。不知不觉走了两三公里,西藏路桥已在眼前。抬头时,前方一栋方形建筑斑驳的西墙突然撞入眼帘。
“上海怎么会有这么破旧的房子?”我暗自纳闷。虽说附近有自家的老房,却因从小随父母在外地生活,这一带并不熟悉。走到近前,见墙面由红与浅灰砖块拼成,左侧“四行”、右侧“仓库”的蓝色大字被风雨洗得发白,方才见的斑驳处,竟是密密麻麻的弹洞。
墙壁前,一块黑色大理石斜铺在地,上面是11个不锈钢大字:“上海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这竟是四行仓库?初中课堂上老师讲过,前几年电影《八佰》拍的就是这里的故事!我第一次发现,历史竟离我的家这么近。
我连忙预约参观,走进纪念馆。6个展区中,一进门的序厅里,谢晋元将军的巨型家书格外醒目:“巧英吾妻爱鉴……我神州半壁河山,日遭蚕食,亡国灭种之祸,发之他人,操之在我,一不留心,子孙无噍类矣。为国杀敌,是革命军人素志也……”字字凿凿,尽显保家卫国的坚定。此外,馆内还陈列着其他战士的家书。
玻璃柜里,《申报》号外泛着黄褐色,“闸北孤军四昼夜抗战”的黑体标题旁,印着士兵们用粮包筑工事的照片:底层门窗全被麻包堵死,二层以上窗口只留半扇,5-10米厚的牛皮、丝茧堆至天花板,像给建筑裹了层铁甲。解说员指着兵力部署图说:“1937年10月,谢晋元率524团1营官兵进驻此处,对外宣称有800人,‘八百壮士’由此得名。”
四行仓库纪念馆内,多组模型定格激战瞬间:日军顶铁板弓身逼近,弹痕累累,气焰疯狂;仓库各处,中国军人或瞄准、或装弹,钢盔蒙尘,面带疲惫却目光坚毅,紧扣扳机尽显守护决心。这些模型串联起战斗碎片,让当年的壮烈与热血清晰可触。
一侧展墙上,一名军官的肖像照片旁标注着“1营营长杨瑞符”。他身穿军服,戴圆形眼镜,眉眼不算英挺,却透着执拗。照片说明写道,其1939年所著《孤军奋斗四日记》中记录:“隔河民众见此壮举,齐声高呼‘中华民族万岁’,声震苏州河。”他还记录了战斗细节:“27日晨,尹排长率两班据守旱桥,敌占北站大楼插太阳旗时,战士们趴在民房屋顶射击,直到弹药用尽才撤回。”日记字迹有些潦草,墨水洇了好几处,像是他回忆战士鏖战时,因情绪激动而手颤所致。
这位四行仓库的营长杨瑞符,难道就是眼前铜梁洞墓地的主人?站在杨瑞符墓前,合川的山风穿过铜梁山的黄葛树林,沙沙作响。纪念馆里陈列的《孤军奋斗四日记》,是他在合川养伤时所写,字里行间的坚定似能穿透时空。1940年春,这位年仅38岁的将军在合川离世,葬于铜梁洞,墓碑朝着上海的方向。
下山时,我忽然惊觉,上海的家离四行仓库不过两三公里,合川的家到二仙观只需10分钟车程。这两个被战火串联的坐标,像两只大手,在我20岁的生命里轻轻一握,让我与那段遥远的历史有了奇妙的连接。
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四行仓库纪念馆建成开馆,杨瑞符营长的墓也同时落成。它们如两座不朽的丰碑,承载着那段刻骨铭心的历史。如今抗战胜利80周年已至,再回望这些纪念场所,意义愈发深远,中国大地的每一寸土地,都浸透着先辈们的爱国热血;他们当年用生命守护的山河,如今已成我们散步的寻常巷陌。那些刻在弹痕里的坚韧,那些埋在墓草下的赤诚,从来都不是博物馆里的陈列,而是流淌在血脉中的基因,在一代又一代人的生命里,悄悄完成着跨越时空的接力。
(指导教师:雷雨轩)
责任编辑:宋宝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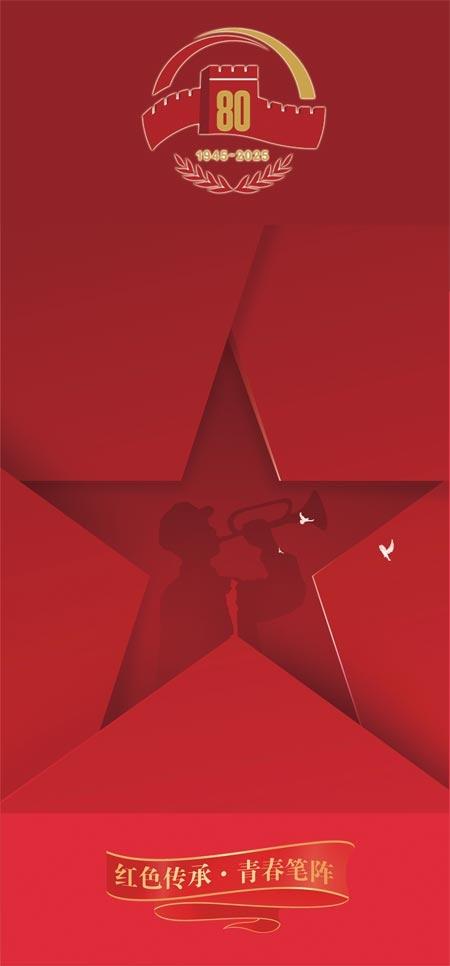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放大
放大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