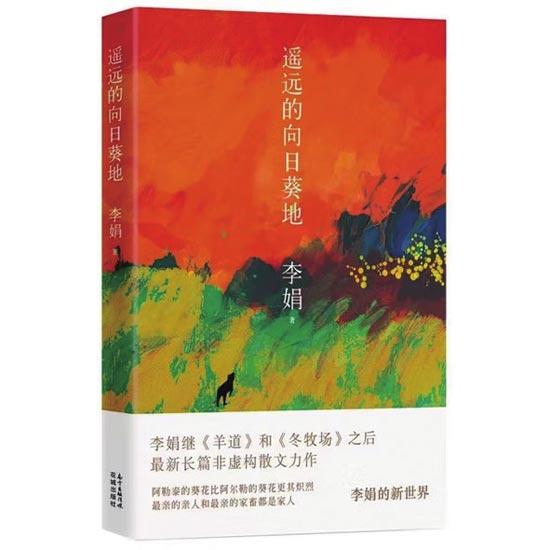
作家李娟的《遥远的向日葵地》收录了48篇散文与一篇后记。在48篇有限的文字里,李娟摘选了母亲与她和外婆在那片葵花地上的故事:第4遍被播下的葵花种子、温柔胆怯的家养犬“赛虎”、飞过茫茫旷野寻找花儿的蜜蜂,在李娟笔下,万物都各有其性格与生活的轨迹,她心甘情愿为它们立一篇篇传。在葵花地里赤身浇水的母亲和李娟心中死于等待的外婆则是散文里时时现身、不可忽视的存在,读者凭着李娟的爱与愧疚去认识她们,像李娟一样走进葵花地的世界。
正如李娟在后记所说,“这是长久以来我一直渴望书写的东西。关于大地的,关于万物的,关于消失和永不消失的,尤其关于人的——人的意愿与人的豪情,人的无辜和人的贪心”。李娟选择了那片“遥远的向日葵地”去书写大地、万物与人,但当读者走上这条通向葵花地的路时,会惊讶地发现万物与大地与人共享着同一份不太精准的时间刻度,在长长久久的时间里通往向日葵地。
伴随着机器的轰鸣,时间的刻度日益精确,人在严苛的分秒之间奔跑,试图摆脱被时间追逐的恐惧。然而,在《遥远的向日葵地》中,读者几乎难以寻觅一份清晰的时间表。李娟并未循着线性、规范的时间轨道讲述向日葵地的故事,而是以故事性时间轻轻掩盖了自然时间的流逝。记录旱年时,她写道:“这是我妈种葵花的第二年。葵花苗刚长出十公分高,就惨遭鹅喉羚的袭击。几乎一夜之间,90亩地给啃得干干净净。”明确的时间刻度被作者有意模糊,转而以人与鹅喉羚之间的生存搏斗填进时间的空白里。
在李娟笔下,时间常常以物候的方式被描绘出来。她写“在葵花还没有出芽的时节里”,并不标注某年某月某日,而是以向日葵的生命节律为时间节点。这种时间的书写,使她的散文文字仿佛浸润着葵花初绽、蜜蜂低飞的画面感,形成一种油画般厚重又温润的质地。李娟用物候取代了物理时间,让散文时间脱离了工业社会所熟悉的纪年体系,而被赋予了一种专属于那片土地的文学性面纱——遥远的向日葵地,遥远的时间。这种时间感的异质性,与城市读者所习惯的时间流逝模式形成了鲜明对照。李娟通过有意拉远的时间距离感,使自然的苍茫与边疆倔强而隐忍的生命力深深渗透进读者的体验之中。
尽管李娟有意回避物理意义上冰冷而精准的时间刻度,她却对“永恒”这一时间单位怀有格外的偏爱。在她的书写中,时间不再是工业化社会的钟表指针,而是一种被缓慢拉长、不断回旋的存在。向日葵地之所以显得“遥远”,不仅源于物候对季节流转的标记,更源自她那种时常向更久远处缓缓回溯的笔法。在《繁盛》一篇中,李娟写道:“我常常想,100多年前,最早决定定居此处的那些农人,一定再无路可走了……我站在冰窟旁探头张望,漆黑的水面幽幽颤动。抬起头来,又下雪了。我看到100年前那个人冒雪而来。”在这段文字中,李娟将现实的感知延伸至百年前,以一种近乎幻觉的方式,在今人与古人之间架起通感的桥梁。漆黑颤动的水面、缓慢飘落的雪花,以及“我”目睹“那个人冒雪而来”的画面,共同营造出一种超越现实时空的静谧与神秘感,百年前的决定与当下的凝视似乎在雪中重叠。这并非单纯的历史追溯,而是一种文学性的“时间复调”。李娟将个体对自然的感知与对祖辈命运的揣想交织在一起,她所书写的“永恒”,是某种沉默而悠长的存在状态——人在风雪中行走的影子,虽然脆弱却恒久,与大地、水面、时间一同颤动,却又始终没有消失。如此无尽之无尽的时间,与辽阔无垠的大地,在这样的时空背景中,又伫立着怎样的人呢?“第九天我离开了。我把我妈、我外婆和小狗抛弃在荒野深处,抛弃了一整个夏天。又觉得像是把她们一直抛弃到现在。似乎这些年来,她们仍在那片广阔的天空下寂寞而艰辛地劳作,而种子仍在空旷的大地之下沉睡。”李娟深切地迷恋着时间的流变与历史的延续。她以爱以愧疚,以人类经由岁月磨损却未被摧毁的柔软情感,自然而然地缝合起过去、现在与未来,使个人情感在时间长河中得以回响。人们于是沿着她牵连起的永恒不息的时间长河,踏入葵花地,踏入自己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直到痛感变成眼泪。
但无论是永恒亘古,还是以物候标记的缓慢时间,李娟的书写目的并非在散文中定格一幅静美、田园牧歌式的旧日向日葵油画。她想要描绘的,是在这遥远时间的流转中,万物与大地持续博弈的过程——人凭着贪心、豪情穿过葵花地,生长与劳作,葵花与人,都金光灿灿地成为了时间的形状。“于是整个夏天,她赤身扛锨穿行在葵花地里,晒得一身黢黑,和万物模糊了界线。叶隙间阳光跳跃,脚下泥土暗涌。她走在葵花林里,如跋涉大水之中,努力令自己不要漂浮起来。”在描写母亲为葵花林浇水的情景时,李娟以其为“整个夏天”冠名。她偏爱这样的表达——“整个九月”“整个夏天”,仿佛在用一帧帧沉甸甸的画面,细细勾勒出时间的质感。时间被离别、劳作与丰收反复塑形,最终沉淀为生活本身。而那句“努力令自己不要漂浮起来”,更像是对时间本质的隐喻。在这片金色洪流般的向日葵地中,人不过是随波逐流的一粒微尘,艰难地在漫长的时间深渊里保持自己的重量,不至于被时间的洪水轻易卷走。时间被她描绘为一种可触可感的存在,是浸润着汗水与泥土气息的生长,是边疆土地上人和葵花共同经历的时间,既缓慢又炽烈,既遥远又亲近。
李娟以近乎悄然的方式,将读者拉进向日葵地的时间里,在那里,时间被重新命名、重新感知。读者终于可以暂时忘却日常生活的钟点计量,凭借李娟构筑的经验世界,触碰在土地、劳作与人之间缓慢发酵的生命时间。
见习编辑:郑欣宜
责任编辑:周伟







 放大
放大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